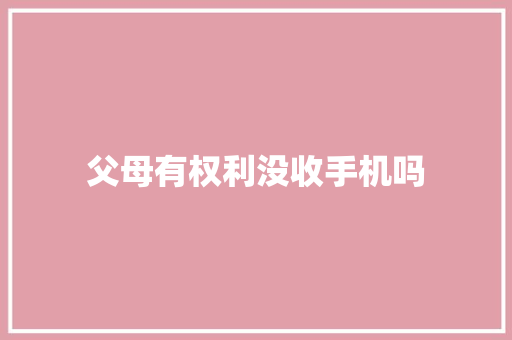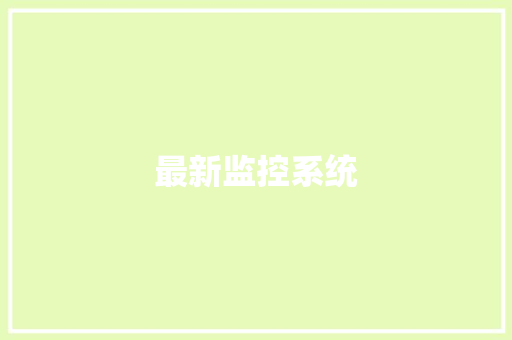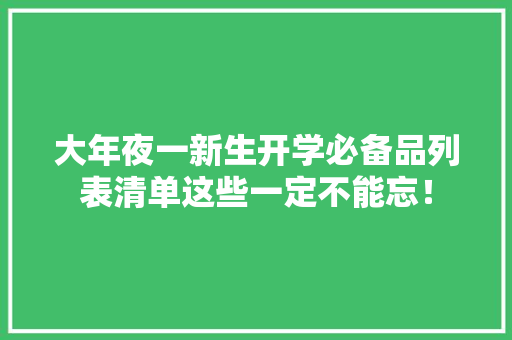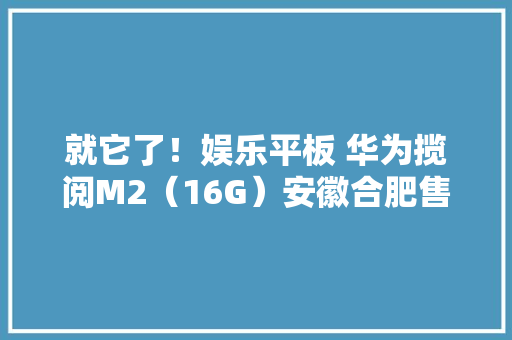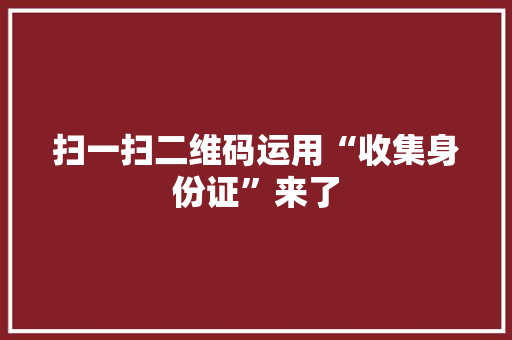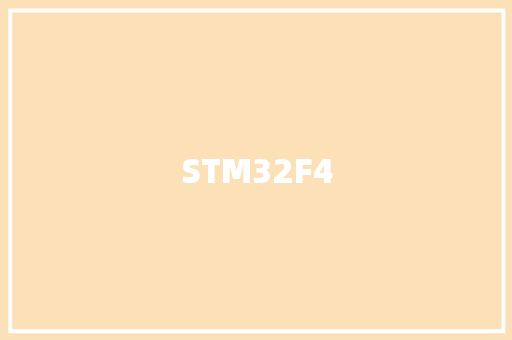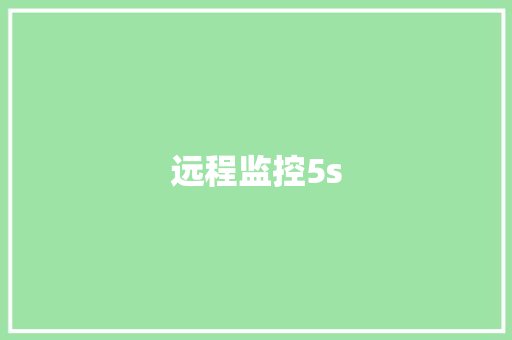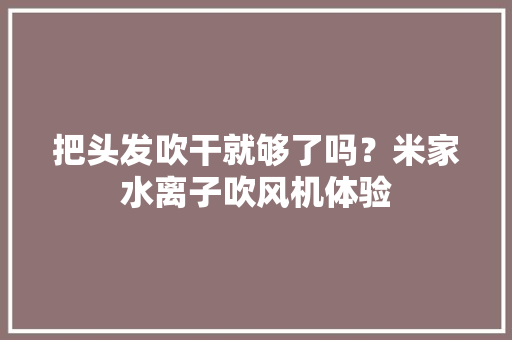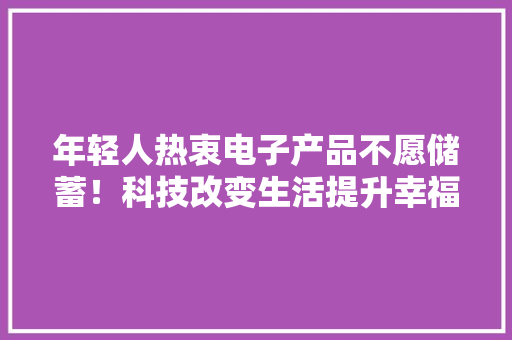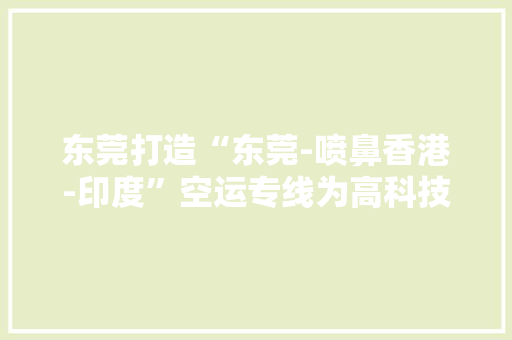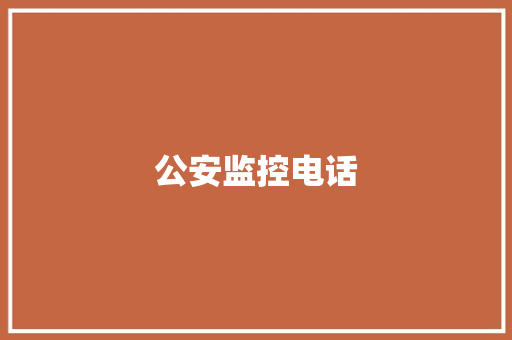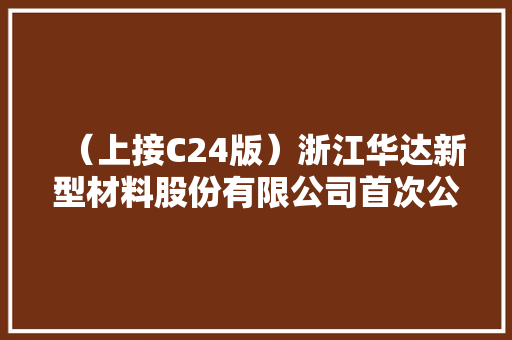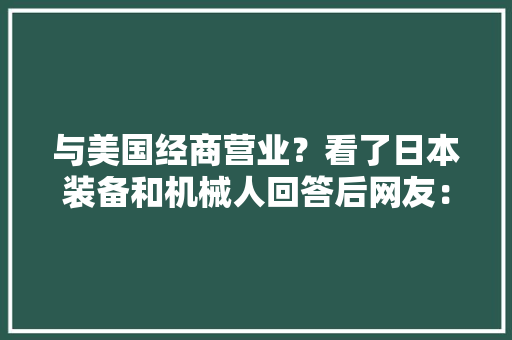英国《卫报》12月15日文章说,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揭橥在顶级期刊《教诲研究评论》上)表明:阅读纸质文本比阅读数字材料更能提高理解力。研究剖析了2000年至2022年间揭橥的20多项关于阅读理解的研究,共评估了近47万名参与者,其结论包括:
长期阅读纸质书对理解能力的提高是数字阅读的数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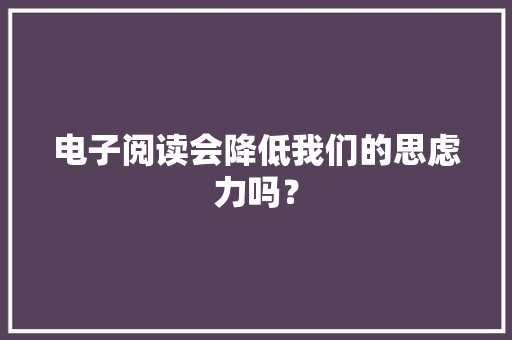
休闲数字阅读的频率与文本理解能力之间的干系度险些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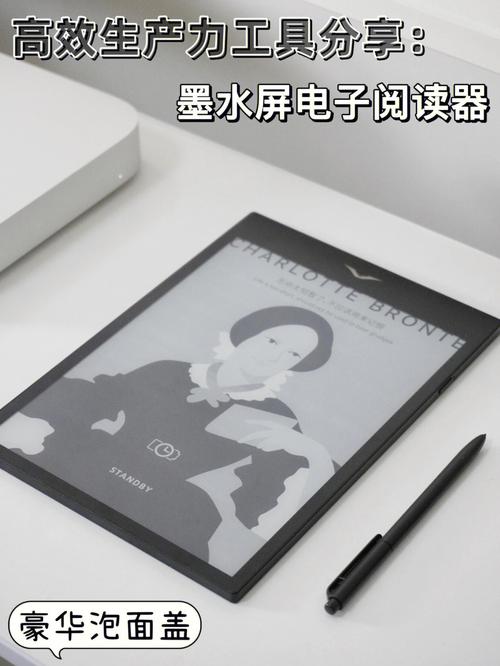
无论人们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基百科等教诲网站上进行阅读,休闲数字阅读与理解力之间的干系度都比较小。
常常进行数字阅读的幼儿学到的词汇较少。
虽然小学生的数字阅读和理解之间存在负干系,但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字阅读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为正干系。
对付上述结论中的征象,研究职员认为缘故原由如下:
数字文本的措辞质量每每低于传统印刷文本,它是会话式的,缺少繁芜的语法和推理。
人们对付数字文本阅读心态更肤浅,一掠而过是非常常见的模式。这可能意味着读者没有完备沉浸在叙事中,或者没有完备捕捉到信息文本中的繁芜关系。
年幼的孩子可能不太能够应对在数字设备上阅读时可能碰着的滋扰,比如忽然收到提醒,我们调节认知的能力在青春期开始进化,幼儿可能还没有完备具备在休闲数字阅读中自我调节活动的能力。
笔者经历了互联网时期之前20多年的文本阅读体验以及之后20多年数字阅读(准确地说是“纸质+数字”稠浊式阅读)体验,就两种阅读模式的效果差异做过多次的切身思考,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的代价紧张还是在统计学方面,对付征象的阐明缺少足够的深度和宽度,须要放在进化生理学背景下去深入稽核。
我们的头脑功能,包括影象、认知与思维机制是进化的结果,它具有进化史遗留下来的范例特色。
这个特色便是:我们的影象和认知具有空间约束性。
原始人的所有影象都是空间具象的,鱼儿巡游的河流在南边,野兽出没的山林在北边,上一次成功的捕猎是在东边的两座山之间的灌木林,去世去的老人埋在西边山脚下,居住在洞穴里一家人有四口,这个数目和一只手上去掉大拇指之外的手指数量一样多,人和动物都在地上,鸟在天上,星星也在天上,神灵出没在从迢遥星光到岩石阴影的每个地方…
在啮齿类动物和人脑的内侧颞叶中存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央的空间定位神经编码模式,其功能源自一组分外的神经细胞--自我中央方位细胞(egocentric bearing cell,EBC),当白鼠在迷宫里探索时,编码构造会逐步建立起来,并根据自身所在位置将对应的细胞点亮,由此形本钱身的方位感知。
(源自网络:EBC在空间影象任务中的浸染)
动物学家创造,即便是智商较低的鸟类也能轻松识别5以内的数量,这实在和鸟类最根本的空间影象能力有关,就数字“3”来说,它可以分别对应“左、中、右”三个位置,而对付这个位置的空间识别是其生存能力的一部分(否则如何躲避天敌?),如在“左、中、右”三个位置中取中点,则得到数字五,这是鸟类对付数量认知的一样平常上限。
进化生理学家罗宾.邓巴研究创造,与普通个体有着最紧密关系的人只有5个,次一级紧密关系的人数是15个,再之后会是50个,150个…等等,各层扩展的比例数值是3。
比拟动物学家和邓巴的研究,我们彷佛可以得出结论,3和5这两个数字是刻印在我们的根本神经机制中的,我们的数字观点来自对空间构造的感知本能。
如果你从小生活在村落庄,高中毕业前都未出过小县城,后来溘然到了相隔千里的大城市读大学,你会在生活一段韶光后溘然创造很难切换回家乡口音,或是很难回顾起中学同学的名字,同样,当你走上社会事情一段韶光,又会很难急速回顾起大学同学的名字,可一旦你有机会在校庆时和同学们回到校园,所有人的名字会溘然像是打开了压缩文件一样平常蹦出来…
之以是如此,是由于我们的大脑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了一种确保脑力高效的影象打包机制:在全新的陌生环境中,大脑会将属于原来熟习环境中的影象暂时打包封存,除非故意识地回顾,否则这些影象不会在思维过程中轻易涌现。
或者可以进一步地说,我们所有的影象,都是具有时空属性的,我们会将所有的经历对应到特定的时空坐标上,在我们的生平中,我们间隔那个当初的坐标越远,与之对应的影象封存得就越深,这便是我们为什么会大量遗忘久远的事情,但在催眠状态下又能够回顾起来。
类似的生理征象在航天员演习时会被特殊关注,在地面环境经由反复演习熟习的操作到了太空环境会溘然忘却很多,为此须要在地面演习时就配以太空环境的视觉仿照。
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你很随意马虎创造,我们头脑中的信息,都是存储在不同的“方位”上,这些方位对应于我们生活于个中的天下的空间构造:伴侣和孩子在身边10米以内,同事和领导在右方10公里外,父母在东南方向1000公里处,昨天读到的一篇故事在右侧书架的中部…
动画片中描写聪明人在思考时,眼球会快速迁徙改变:眼睛一转,计上心来。
这是由于我们在快速地探寻我们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天下的空间构造模型以及存储在模型中的信息。
与生活影象类似,我们的阅读影象也具有空间约束性。
影象基于联系,就好比我们背单词,联系的信息越多,影象越稳定。当你回忆不久前读过的某本小说集中的一篇故事,你一定会想起读到它时自己的状态:从书架上中部取下它,在客厅靠近阳台的沙发上,在周末上午的阳光里,等等,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你对书中内容回顾的一部分。如果你出差到了外地,想起这篇故事,你还是会将这篇故事“存储”在千里之外的自家客厅的书架上,你想起它,就会同事想起那个位置,彷佛它不但是一个故事,而是一块卵石,它必须也只能呆在某个位置。
回忆一下中学时读过的课文,你想起什么?只是课文本身吗?你一定会想起你的学校,你的教室,乃至是老师读这篇课文时的声音,彷佛这篇课文只属于10年前的那个教室。
这可不是大略的影象关联,而是我们的影象实质。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了一个长长的时空森林,我们将所经历的统统,以及籍由这个经历所学习到的所有知识都安置在了这个森林中的某个确定位置。
其余,纸质书有厚度、长度和宽度,它占去了小小的空间,当我们翻阅一本书时,便是在探索这个小天下,作者和出版商深刻理解这点,因此,从封面到扉页到章节排布和插图,无不是在布局和丰富这个天下的内部空间,纤薄的扉页上的几行笔墨带给我们的感想熏染不同于装裱华美的封面,其差别就像内庭花园和大门的差异,而面对超过500页的一本书时,我们的感想熏染就像面对一座高山或是一大片森林,我们一页一页的翻看下去,右手上的重量逐渐地转移到左手上,这种觉得就像翻过了山顶走到了另一边,而书中的每一段笔墨彷佛都散布在我们路子的道路上。
因此,纸质书的内部物理空间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影象框架,我们不但是记住了所读内容存在于那本书中,还会记住它存在于书中的某个位置,就像记住了某棵树在树林中的某个位置一样。
其余,一本书纸质书的品相也会成为所读内容的渲染。
我最近从旧书网淘到一本小说,说的是一个源自非洲冈比亚地区非洲原住民的美国家族三代人的传奇历史,书出版于30多年前,封面书脊都有些磨损,翻开内页会闻到一股熟习的村落庄泥巴屋子的奇异气息,而书中主人公也正是出生于这样的环境里,这带给我一种强烈的错觉,彷佛这本书曾陪伴过主人公。
总而言之,纸质书是一个现实中的实体,它拥有实体的繁芜特色与内涵,所有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影象的一部分,进一步地说,它的实体特色不但是与书中内容仅具干系性的一部分,而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我们失落去了什么?
当你捧起一本书时,你捧起的是一个天下,你能够像上帝一样俯视它,用你灵巧的手指随意进出任何一个地点,但面对电子书,这很困难,这时候你成了等在窗口前的一位顾客,在没有目录的情形下,如果要翻到你10页,就必须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翻一次就要等待一下。
当我在手机或阅读器上翻页时,生理总有一种缺失落感,这种缺失落感来自对纸质阅读的影象:纸页在指尖翻过期,彷佛推门从一个房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影象的坐标也随之变换了空间位置:读过的都在左边,未读的都在右边,随着韶光流逝,左边的越来越厚,右边的越来越薄,就像在穿越一片丛林,出发点越来越远,终点越来越近,所读的内容在影象的空间里划出了一条线,从封面到封底的每一页都排列在这条线上,并根据其位置具有了不同的色调和温度,就像岩穴的洞口和洞底具有不同的亮度和温度一样,对付一本常常翻阅的短篇集来说,第一篇永久是透明的,它是你院门口的一块青石,而中间的那几篇永久是晦暗的,它是寝室灯下的一个小沙发,但在电子书上,你找不到这样的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右手边,都在一个平面上,在影象的空间中,它们拥挤在一起,相互重叠交错,不同的声音和色彩殽杂在了一起,你很难将它们各自归位。
这大概能够阐明为什么电子化阅读降落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即便我们的阅读不是碎片化的):我们接管的信息在脑内存储的机制不良,它们大量拥挤在一起,很难有效组织起来。
进化的困境:电子阅读的未来
我们的左脑卖力措辞和逻辑,右脑卖力空间和想象。
在阅读纸质书时,我们的旁边脑都会被充分调动,左脑卖力解读笔墨,右脑卖力影象它在书中的位置,但在阅读电子书时,右脑卖力空间影象的功能区的激活水平较低,这会导致大脑整体的生动水平降落。
如果我们是在手机上阅读一条新闻,我们会将新闻内容映射到这个天下的某个时空点,以此形成空间影象,但如果阅读的是一篇科学论文,能帮助我们影象的就只有我们的逻辑能力了,或者,我们须要调动所有的遐想和通感来将提高影象水平。
对付孩童来说,它们的脑功能更多表现为右脑能力,基于逻辑的内容理解和影象力尚未得到发展,因此在面对电子书时,影象和理解效果会受到影响。
如果是成人,情形会有所不同,我们有了丰富的天下知识和生活影象,在阅读电子书时,面对在一格平面涌来的大量的信息,我们能够在影象的空间中为它们找到得当的位置,通过对付信息的系统化组织来提高理解和影象。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未来的情景,如果纸质书都消逝了,一个人从小就不具备阅读纸质书的条件,他能在完备平面式的阅读中发展出良好的影象和理解力吗?
我相信可以,这只是一个神经系统适应性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即便一个人从小不能够生活在三维的天下中,只能从一个电子通道进行阅读,他该当也能够发展出独特的理解办法,这是这种理解办法对付我们而言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就像我无法想象海伦.凯勒的天下一样。
幸运的是,这样的未来大概不会涌现,即便纸质书完备消逝了,电子阅读办法也绝不会勾留在发光的玻璃平面上,我们已经有了虚拟现实,我们正在开拓脑机接口,我们大概还会拥有更多的办法实现与天下的接入。
何况,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舍弃对纸质书的热爱,它就像地皮、花朵和天空的云朵一样,是我们所爱的这个古老天下的一部分,也是关于人类理性与知识的表现艺术,其丰富的表现形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
参考阅读:
Neuron长文解读:揭秘第一人称视角在空间定位和影象中浸染的神经编码机制 - 知乎 (zhi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