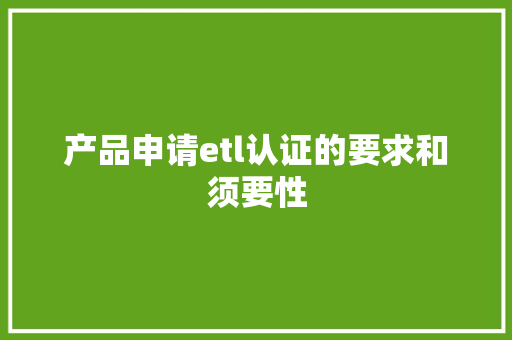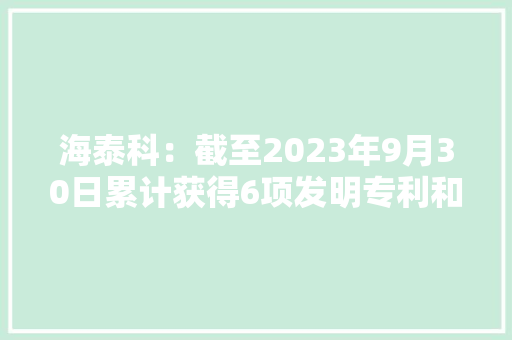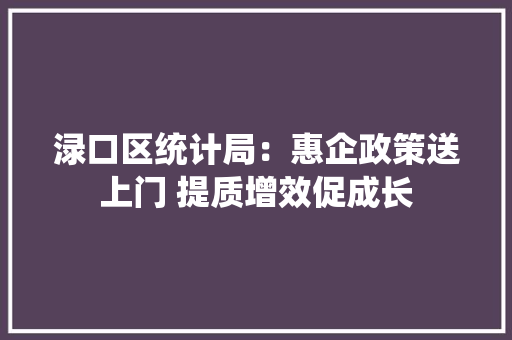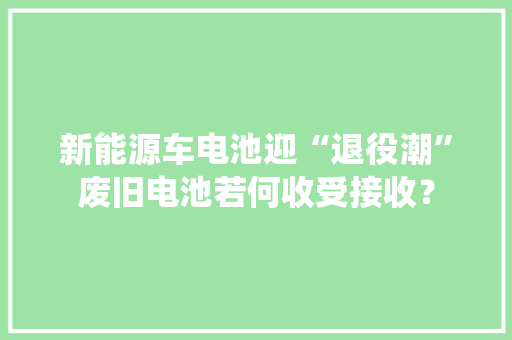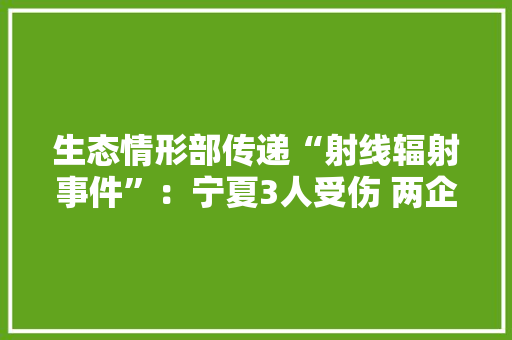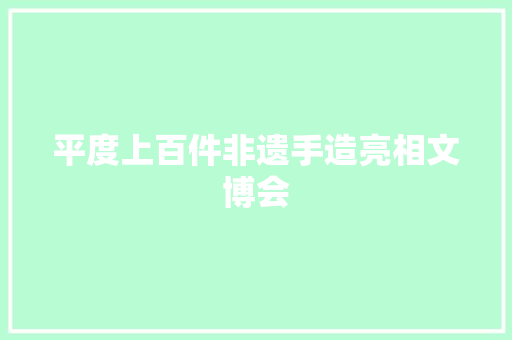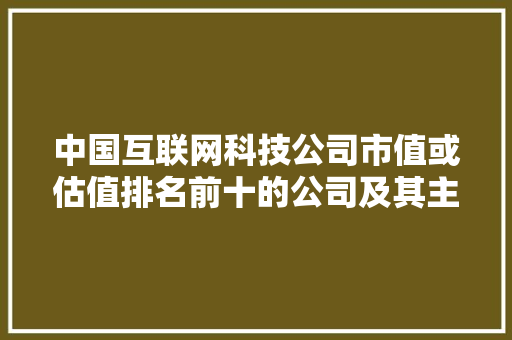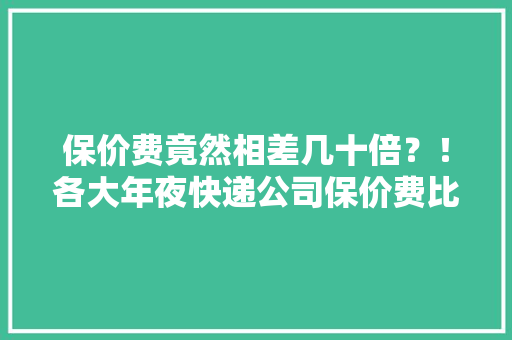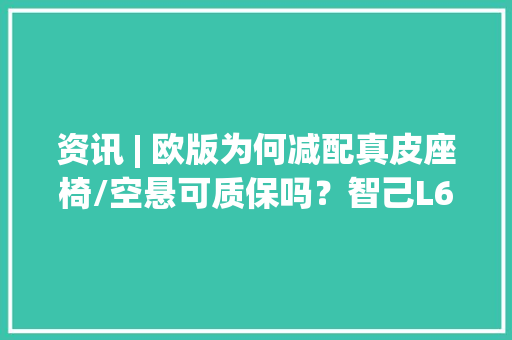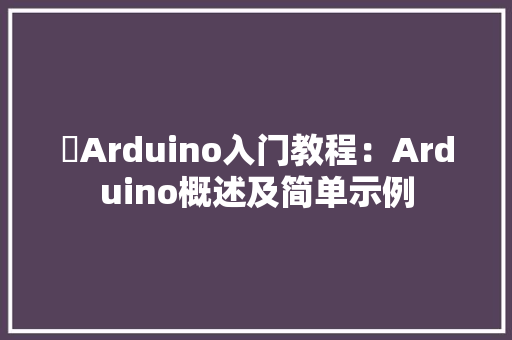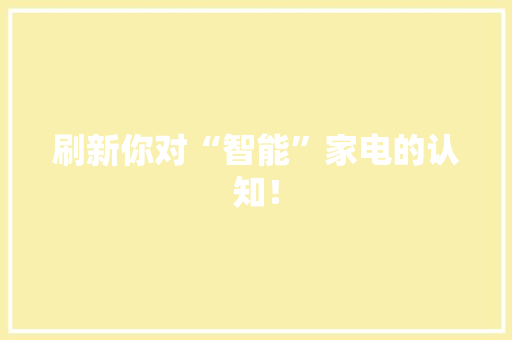王夫之认为,“大有”的意思是能够保有众大。大指众阳而言。《大有》五阳爻,只有六五一阴爻。阴爻而居尊位,象征懦弱之君。懦弱之君何以宰执强梗不易低头之臣?王夫之的答案是,虚中柔顺,善体下情,以此肃清臣下的疑惑、阻滞之心,才能使群臣统于自己之下而为之主。也便是说,主上之以是亨通,是由于得到浩瀚能者的赞助。《内传》将此总结为“以柔道通天下之志”,并点明此为创业之始最主要的原则。
同样的意思王夫之在对《同人》卦的阐明中也表露得很清楚。《同人》卦也是五阳一阴,不同者在《大有》为六五,《同人》为六二。依一以统众之释例,《同人》亦可象征君臣关系。在阐明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一句时,王夫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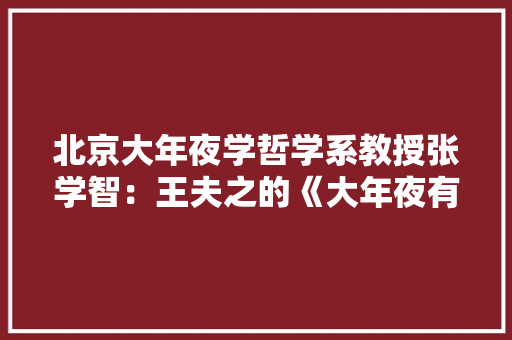
“同人”者,同于人而人乐与之同也。刚者,柔之所依,一阴固愿同于众阳;柔者,刚之所安,众阳亦欲同于一阴。凡卦之体,以少者为主。二者,《同人》之主也。柔而得应,无离群伶仃之心,而少者,物之所贵而求者也,则五阳争欲同之矣。“于野”者,迄乎疏远,迨乎邱民,皆欲同之之谓。为众所欲同,其行必“亨”。柔非济险之道,而得刚健者乐于同心,则二之柔既足以明照安危之数,而阳刚资之以“涉大川”,必利矣。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意思是《同人》卦的精义在,只有乐于同人者,人方乐于与已同。以君臣言,二者为相倚关系,君为臣之所依,臣为君之所倚。同人仅六二一阴,虽属劣势,但为众阳所求,故虽危而安。同时六二与九五相应,表示其无离群伶仃之心而为众阳所戴。于是君臣同心,一体固结。“同人于野”者,象征君主不仅得到众臣的推戴,而且得到草野百姓的推戴,故其行一定畅通。二之阴柔虽不敷以自抜于险难,但得到浩瀚刚健者的同心拥护,君民共济,大川可涉。王夫之这里强调的是,君臣齐心专心,君民齐心专心,互为依倚,则险难可济。
但他同时指出,所谓“同人”,不是乡愿之同,而是君子之同。君子之同者,非容悦诡随,一味迁就,或以利而合,损失道义。“同人”须以义为原则,在义的条件下求同。故王夫之说:“君子之利,合义而利物也,非苟悦物情而所欲必得也。”
在对《同人》彖辞“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一句的阐明中,王夫之也对此意加以强调:
具此三德,故人乐得而同之。二正应在五,不言应刚而言乾者,人之志欲不齐,而皆欲同之,则为众皆悦之乡原矣。唯不同乎其情之所应,而同乎纯刚无私之龙德,以理与物相顺,得民气之同然而合乎天理,斯为大同之德,而非苟同矣。
所谓“三德”,指得位、得中、与乾所代表之天相应。王夫之特殊指出,三德中之应乎乾最为主要。由于乾代表天,应乎乾即主动将自己纳于天道天理的约束之下,以天理为自己行为的范导。详细到“同人”,无天理规范的攒聚,则陷于无原则之滥交,则为媚谄众人的乡愿。只有以天理物情为原则的交往,才是君子之交。
在阐明《同人》彖辞“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一句时王夫之也指出:
“文明”非暗私之好,刚健非柔侫之交,君子之同,同于道也。同于道,则“能通天下之志”,而天算夜同之。小人之以是同天下者,苟以从人之欲。而利于此者伤于彼,合于前者离于后,自以为利而非利也。
“文明以健”指《同人》《离》下《乾》上,离明而乾健。“中正而应”指六二居下卦之中,而与九五相应。故“文明以健,中正而应”指《同人》之六二。此中六二为一卦之主,象征君。王夫之此段讲授对君主之如何得臣、得众提出了基本原则:君子之同,非小人之同;同于道,而非同于利;无私之同,而非怀私之同。君子之同,不同于乡愿之同。乡愿之同,是无原则的诡随、谄媚以求合于时风众势。君子则独立不倚,一以道义为归;不徒求合于人,而求合于道。不求附于己者多,而求合于己者正;不是出于私己之利益求合于众,而是出于道义之任务,求合公众年夜众之利益。王夫之在这样的高哀求下,提出了君主何以提高辨别能力,既最大限度地联络同人,又严守道义,不与小人与世浮沉的艺术,这便是他在阐明《同人》象辞“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时所说的:
火在天中,以至虚含大明,明不外发,而昭彻于中。人之贵贱、亲疏、贤愚,物之美恶、顺逆、取舍,无不分以其类而辨其情理,则于天下无不可受,而无容异矣。大明函于内,而相容并包,以使各得明发于外,宪天敷治,而赏善劝善,以统群有。存发之道异,高下之用殊,《同人》《大有》,君子并行而不悖也。
《同人》象辞仍就内外卦所象征的事物着眼。《离》下《乾》上,象征火在天中。火者,明昭;天者,太虚。故火在天中即“至虚含大明”。王夫之就此义发论:至虚含大明,故无有障蔽,中之明照彻于外,人与物之性子、功能、相互干联、代价秩序等各个方面皆别辨清晰。因中央虚廓无窒,故天下物皆一体容受,无有隔碍;因大明函于内,明察人与物之美恶、是非,故能兼容并包。明在天中,又表征聪慧以天理为根本准则。在此准则约束下,君仁臣忠,众人效命,以成大美之治。王夫之还提出,《同人》与《大有》,前者主联合志同道合者,敷施发用,后者主积累致大,立于不败之地。故两者可以兼取为用,并行不悖。
从这里的讲授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南明政权偏安一隅,势危力弱,但又君臣猜忌,党争激烈之时,主见君主虚怀明睿,广泛容受各种不同政治势力亲睦处集团,风雨同舟;臣下则各思报效,展其才情为君所用,而又赏罚分明,培植好的政治秩序。王夫之特殊强调象征积蓄力量的《大有》与象征风雨同舟的《同人》并行不悖,便是欲在清兵已经掌握大局,南明政权苟延残喘于东南一隅的情形下,内部联络齐心专心,肃清党争之害,积聚力量,以图后举。而欲达此同的,永历帝的“大明”即虚怀能容、明察形势最为关键。
但王夫之又根据现实政治中君主暗弱,威势不敷,为权臣悍帅所劫的现实情形,强调君主不仅要虚中柔顺,明察形势,还要树立威权,刚猛行政。故王夫之认为,与《乾》之“元亨利贞”四美皆具比较,《大有》之“元亨”,尚未达圆满之境。尚有不敷,此不敷即在主政者缺少威势与激厉迅奋。王夫之说:
众刚效美于一人,乾道大行,故有《乾》“元亨”之德。而不言“利贞”者,无刚断以居中,未能尽合于义,能有众善而不能为众善之所有,则不敷以利物。柔可以顺物情,而不能持天下之变,泛应群有,未一所从,则其正不固也。
王夫之不满《大有》卦之整体势用者有二,其一,《大有》六五,以阴居刚断之位,有窃居阳位之嫌,此不合周易阳刚阴柔、阳主阴从之义。其二,阴不能长居君位而持天下之变。阴虚中柔顺以怀集众阳,消其疑阻,皆事物初始之义。而事物逐渐壮大之时,非阳刚做主行权不能善终。阴初始可以柔顺下人而为众阳所拥护,但在逐渐壮大的上进程中对繁芜事变之应对,则非阴柔所能办。阳柔在顺应物情上有其长,而在应对大事变、驾驭大波澜上常刚断不敷。故必逐渐失落逝世人之心,拥护变为疑阻。这一点王夫之下面一段话说得很清楚:
此卦之德,王者以之屈群雄,绥多士,致万方之归己;而既有之后,宰制震叠、移风易俗之事未遑及焉。君子以之逊志虚衷,多闻识以广德,而既有之余,闲邪存诚、复礼执中之功犹有待焉。盖放学之初几,兴王之始事也。因此六五虽受天佑,而致“易而无备”之戒焉。
王夫之的这一补充实含深义。众刚效美于一阴,在王夫之看来并非常道。他肯认的是阳刚做主,众阴听命。九五之尊,不容农历久窃居。众阳效美于阴,乾道藉以大行,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常道须阳刚居中,阴柔顺从。故虽能主持于一时,但不能长久居领袖地位。这也便是《大有》卦辞为何不像《乾》那样直言“元亨利贞”而仅曰“元亨”的道理。
这里王夫之除了表达出对永历政权恨铁不成钢的生理情绪之外,还透显出一个主要的情结预设,即他一向反对的女主、戎狄为天下主。虽然《大有》就卦德、卦才来说是很好的,但以阴为众阳之主,虽“大有”而仍有缺憾,故判之为“未能尽合于义”。“能有众善而不能为众善之所有”,亦暗含众阳终不能雌伏于一阴之下俯首听命,终将有所作为而冲破女主之抚有之意。
二王夫之《大有》诠释的第二个要点在对明亡之后士人何以自处这一主要问题的谈论。这个谈论是借对《大有》初九的讲授展开的。王夫之在阐明初九爻辞“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一句时说:
“无交”之害,岂有幸哉!
然而可免于咎,则何也?无托而固,不亲而免谪者,其为阳乎!
处散地而自保,履危地而自存,逃亡于恩膏之外,傲立于奔忙之交,自有其有者,义不得而咎也。无交者,阔别六五权力中央,伶仃而不亲,无有可依托之人;置身于隐微之地,恩情不被及,又不愿攀援上交,诚弱小无援、不为人知之时。此种形势,可谓艰矣,而艰则无咎。有为之人,处此艰危之地,自我特立,保持不懈,自养其志,自培其能,不希求私幸,不奔忙朱门。全凭一己之力独立撑持,以克时艰,以待定命之转。这是王夫之所持的儒家士君子处艰危的态度和方法。
王夫之又指出,在此艰危形势下,士人随意马虎走入另一极度:傲岸得意,不为君用。王夫之主见,在清平之世,该当遵照孔子“邦有道,不废”之义,出仕任事,不能做严光、周党之类的隐君子,不为世用,徒博高名。以是王夫之在讲授初九象辞“《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一句时说:“昔时夜有之世,而居疏远自绝之地,则害君臣之义。”意为,“大有”之世为治世,明君理国,君子臣大有为之时。纵然在艰危不利出仕之时,亦不能放弃儒者的操守。王夫之对《遁》卦的阐明,颇可表明此种志向。如在阐明《遁》卦卦辞“遁亨”时,王夫之说:
遁亨者,君子进则立功,退则明道,明哲保身,乐在疏水,于己无不亨;而息玄黄之战,以勿激乱,且立风教于天下,而百世兴焉,于天下亦亨矣。
这是说,君子审时度势,可以出仕亦可以遁世。出者建文治武功于当世,遁则明哲保身,栖于山间林下。遁是为了息争斗,远乱离,不徒为保身家性命。故遁非高眠林泉,无所事事,而是息影人间,另图大事,暂退一步,以待后动。在王夫之看来,这样的隐居,因此退为进,以隐为显,从道义上说是尽伦尽制的,是行道的一种弯曲表现。这样的遁世才能为后世立风教之榜样。其余,此种隐遁,是潜龙勿用,苦志磨炼自已,故在隐遁中仍须履礼行义,如出仕建功时一样。他反对的是庄子笔下的隐士,此种人抛弃士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不见大道的一曲之士。王夫之说:
消心于荣宠者,移意于功名;消心于功名者,移意于分义。大人以分义尽伦,曲士以幽忧捐物,古有之矣。道之所不废,则君子亦为存其人矣。然而礼者自履也,行者自型也。合天德之潜龙,行可见之成德,其庶几焉。若夫土木其形,灰槁其心,放言洸瀁,而托于曳龟逃牺之术,以淫乐于琴酒林泉,匪艰而自诧其无交,被衣、啮缺之以是不见称于贤人。
这一段话大有深意。王夫之认为,在浊世保持名节,实大不易。在小人当权,大道不通之时,忠臣可以抛弃朝中之荣宠,而寻求立功他乡,扬名疆场。如果此亦不可得,则暂时隐居。而隐居是权宜之计,不得已之选择。隐居不是逃离人间,可以任意放肆自己,而是隐居之时仍不废伦常位分。此时之位分,紧张是君臣之分。不忘君臣之义,不忘对国家应尽之责任,时时准备待机而出,以图报效。这便是王夫之的“大人以分义尽伦”。大人者,儒家士君子之人格;分义者,其职位名分所当尽之责任。尽伦者,尽此伦常关系中所哀求于人臣之责任。只要大道尚未彻底崩解,士君子即抱剥时争复、否时争泰之志,不消极沉沦,不绝望放弃。此时士君子应以《乾》卦之“潜龙勿用”以图“见龙在田”为辅导自己行为的方针,隐居但履行应有的行为规范,以慎独自我约束,不自我放逸,不自甘堕落。王夫之鄙夷在国家危难时躲避责任,为保身家性命,视弃君臣之伦如弃敝屣的士人。至于《庄子》笔下被衣、啮缺那样的隐士,更为王夫之所不屑。由于这样的隐士,在国家清平时即放弃对国家、民族的任务,逃世得意其乐,隐居于山间林下,琴棋诗酒遣日,并以此自高、以此夸耀。这样的隐士是儒家所不许的。
在《周易内传》对《遁》卦“遁之时义大矣哉”一语的阐明中王夫之也说:
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亢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幸,孟子所谓小丈夫也。非精义乘时者,无由以亨。
王夫之认为,隐居一道,古今皆有。但隐居有时、有义。巢父、许由亦被衣、啮缺一类人物,其隐居即不合时宜。由于尧舜之时是盛世、治世,有才而不为盛世所用,不以一己为世事尽力,不属躲避便属自私,为君子所不道。而严光、周党一类人,其隐居不但不合时宜,亦不合君臣大义。皆孟子所斥之小丈夫。王夫之反复强调,“遯之时义大矣哉!
”非义精仁熟而又长于驾驭机遇者,是不能做到进退有据的。王夫之借《周易》对隐遁之义的阐发有取于程颐。《程氏易传》在对“遁之时义大矣哉”一句的讲授中说:
遁者阴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贤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若有可变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处遁时之道也。
这段话代表程颐对小人性长之时君子的应对之策。意思是,君子于此种苗头初萌时即应及时见出,而深有戒备。不特此也,君子在大道将废之时,必不肯仅全身自保,而思救此危局。当危难浓重之时,救治的办法是不使危难达于极点,力争增强君子衰弱之力,设置障碍遏止危难扩大。假使能图得一暂安局势,君子并不放弃。比如王允之于汉末之危局、谢安之于西晋之危局,皆勉力使之小安以争取旋转大局的有利机遇。《遁》卦所讲的,是小人势焰正炽君子宜于遁避之时。处此之道,不能悲观退避,而要积极挽救。须不舍小善,点滴积累,积渐成大,旋转危局。
程颐这种识见为王夫之所吸取。他在《周易》阐发中大力表彰君臣大义,贬斥为保身家性命而隐居,便是号召知识分子在明已亡而南明尚在苟延残喘时,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力争规复明朝。纵然明朝不能兴复,也不为新立的清朝干事,宁肯隐居著书。王夫之坚信中华文化不会亡于戎狄之手,坚信中华文化将来必定重光。王夫之对隐遁之义的阐发,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为延续文化命脉而做的切实努力。
三王夫之以上对付体用理论的阐发,终极落实于《大有》九二爻辞之阐明。个中暗含的现实关怀是君何以得众和权臣何以自处。王夫之说:
但是其义何以见之于大有之二也?大有者,有也。所有者阳,有所有者阴。阳实阴虚,天生有而火化无。二为五应,为群有之主,率所有以实五之虚,二之任也。乃有以实载虚,以生载化,则有群有者疑于无,而与天地之藏不相肖。故推其任于二,而责之备焉,曰,非其积中也,败固乘之,而亦乌能免于咎哉?“无咎”者,有咎之辞,二以五之咎为咎,斯不咎矣。故五以“交如”发志,因二以为功也;以“无备”须威,内反而不敷也。《象传》之以败为戒,岂为二本位言之乎?
这是说,“大有”阐发的,是“有”之义。但《大有》的卦像是五阳一阴,按《周易》五为君位、以一统众的阐明体例,六五虽阴,但为有所有者,余爻虽阳,但为六五所有者。阴为隐,阳为显。就由用以得体言,体为隐,用为显。阴虚阳实恰好印证了由用得体。从高下卦体言,内卦为《乾》,外卦为《离》,《乾》象征天,《离》象征火;天主生,火主化,天所生之有,为火所化而无。但此“无”绝非空无一物,而是在生灭变革状态中。“有”是征象,生灭变革无时或停是实质;“有”为暂时的、可把捉的履历之物,“无”为变革中的、不可把捉的本体中物。就此义说,亦由用以见体。
王夫之还认为,九二与六五为应,余爻则无应,故九二为众阳之主。九二率领五阳以归附六五,其浸染为以众阳之实补充六五之虚。而九二爻辞“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则九二完备可胜此任。故王夫之对九二此句的注释是:
九二刚而居中,为群阳之所附讬,皆唯其载之而行。才富望隆,归之者众,有与五分权之象,疑有咎矣。然上应六五,不居之以为己有,而往以输之于五,则迹虽专而行顺,不得以逼上专权,辇众归己而咎之。
从迹象上说,作为主宰者,驾驭众阳之六五形只影单,伤于孤零,为九二所载、所化,因而与作为万物本体的熟年夜、深厚不相配。但六五的高明之处在将己寄讬于九二,并责其完本钱应由自己完成的职分。九二以六五之咎为己之咎,努力承当,积中以厚,载物以劳,故化咎为无咎。王夫之就此加以评论:“诚信之输于五者积于中,则持盈而物莫能伤。后世唯诸葛武侯望重道隆,而群策群力,以事冲主,能有此德。”意思是望重位尊足以震主而仍推诚相见率众臣竭忠尽诚以辅佐幼主,无丝毫篡逆之心者,唯有蜀相诸葛亮能之。但王夫之论证更多的不是忠实为主之九二,而是作为主宰、本体的六五。认为六五之以是服众,之以是能使九二率众附己,全在于其虚己待下,胸襟磊落,以信义服人;且能不失落其威仪,柔中有刚。由此导致君仁臣忠,不相猜忌,相辅而行,各极其用的局势。王夫之在阐明《大有》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时对此义大力发挥:
“厥孚”,阳自相孚也,故曰“厥”。“交如”,交于五也。五虚中而明于任使,其俯有群阳也,以遁物无违之道,行其坦易无疑之心,众皆愿为其所有。群阳相孚以上交,道极盛矣。而又戒以“威如”则吉者,五本有德威存焉,但众刚难驭,虽大公无猜,而亦必谨高下之分以临之,益之以威,初不损其柔和之量,而无不吉也。
在对六五象辞“‘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一句的阐明中也说:
虚中柔顺,乃能笃信于人而不贰。其于物多疑者,必其有成见以实个中,而刚于自任者也。六五孤阴处尊位,抚有众阳而不猜,其信至矣。“发志”,谓感发众志而使归己。“易”,和易近人。“无备”,不防其僭逼也。创业之始,动听心以和易,而久安长治之道,必建威以消萌,《大有》之所未逮,故不敷以利贞,而又以“威如”戒之。
将《外传》与《内传》参合而不雅观,王夫之的意思是很显著的,二与五象征君臣,六五为孤阴,表示君主懦弱势单,其浸染在以九二为首的五阳。五为体,二为用,五必靠二为之彰显,二必靠五以为俯宰。相互倚伏、由用以见体的意思十分明显。
这里的阐明十分主要的是,君臣互倚输诚为国的意思为王夫之晚年所作的《周易内传》所发,实有对南明史实的反省之寓意在内。王夫之生当浊世,乡试中举后,因战乱不能北上会试,躲兵祸于四方。虽欲有所作为,但无缘施展才略,生平只在南明桂王永历政权中受过短期间的官职。而永历政权在残山胜水间犹党争激烈。桂王暗弱而又骄横,大权操于悍帅之手。王夫之所希望的是,君暗弱之时,须客气听取大臣见地,信赖大臣,勿起猜疑,大臣奋起效命,共济时艰。此即“五虚中而明于任使,其俯有群阳也,以循物无违之道,行其坦易无疑之心,众皆愿为其所有,群阳相孚以上交,道极盛矣”之意。同时,君须有其威严,虽在危难惶遽之时,君臣之分不能淆乱,君须时时以威势镇悍将,不使其搪突不听节制。此即“五本有德威存焉,但众刚难驭,虽大公无猜,而抑必谨高下之分以临之,益之以威,初不损其柔和之量”之意。对付臣子,特殊是握有大权、社稷安危系于一身之重臣,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王化澄、李成栋等,王夫之则希望他们以永历政权的安危存亡为重,肃清勾心斗角、嫌隙日生乃至为争权夺利自相惨杀的局势。重臣须不负众托,集众人之意志,忠心为国。这便是王夫之所说的“九二刚而居中,为群阳之所附讬,皆唯其载之而行。才富望隆,归之者众,有与五分权之象,疑有咎矣。然上应六五,不居之以为己有,而往以输之于五,则迹虽专而行顺,不得以逼上专权、辇众归己而咎之”之意。王夫之对君臣双方皆有哀求,目的在使君臣一体同心,共图明室之兴复。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空想,寄寓在他对《周易》的发挥中。
其余,王夫之在《外传》中所侧重的,与在《内传》中所侧重的,有所不同。王夫之于桂王永历四年(1650)仲春至梧州受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之职,到十一月离开桂林瞿式耜留守府奔母之丧,实际在永历朝为官约十个月。亲历永历朝政治之险恶,并因弾劾权臣王化澄差点丢了性命。对君臣关系、系命大臣与众臣之关系深有体会,并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反省、发酵。后五年,王夫之作《周易外传》,将此切肤之痛写入书中。但此时避兵惶迫,未暇详论,只简短提到:“二以五之咎为咎,斯不咎矣。故五以‘交如’发志,因二以为功也;以‘无备’须威,内反而不敷也。象传之以败为戒,岂为二本位言之乎?”以六五与九二之关系发挥君臣大义,意思是,臣须以君之安危为己之安危,才能助君得到安全之地从而自己也得安全。但君须以不疑之心信赖臣下,此目的才能末了达到。同时君须建立威势,才能有效驾驭臣下,此为达到君臣同安之末了目的的主要担保。九二象传所告诫的“大车以载,积中不败”,表面上是就臣言,而实际上是就君言,所谓“臣足,君孰与不敷”是也。这些意思皆粗略言到,而到晚年的《内传》中,将从前蕴蓄于胸中不断翻滚、发酵的这些意思畅论发之,故较《外传》尤为深刻。因是详注文体,逐爻讲解,故许多弯曲微细的意思得以深度论析。如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王夫之注曰:
九三居内卦之上,为三阳之统率,而三为进爻,率所有之大以进于上,公领其方之小侯,修贡篚以献天子之象也。乾健而阳富,席盛满之势以上奉柔弱之主,自非恪守侯度之君子,必且专私自植。故言“小人弗克”,以戒五之慎于任人。
对君弱臣骄的形势下臣须守臣之侯度,不专权,不造就私人,君须明辨君子小人,任官须慎之又慎之意重言表出。又如九四爻辞“匪其彭,无咎”,王夫之注曰:
彭,鼓声也。鼓声以是集众而进之。四阳连类,四居其上而与内卦相接,疑于众将归己。乃其引群阳而升者,将与之进奉九五而使之富,非号召众刚使戴己也。故虽不当位而无咎。
九四离五最近,象征帝王身边之重臣。此段阐明乃明言告诫握重权之人,须将众臣对己之推戴引到对君的忠实上去,这才是为臣之道;若乘此有利于己之机遇结党营私,则将招来杀身之祸。故在对九四象辞的注释中又申明此意:“居疑贰之地,必别嫌明微,以昭君臣之定分,而后可无咎。”可以看出,王夫之晚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是,明朝因党争而亡,阁臣的争权夺利是罪魁罪魁。南明因各种政治势力反面而失落去许多规复之机,各路主要人物的相互疑忌不能精诚互助是败事之阶。王夫之有见于此,借《周易》诠解,对他所希望的君臣关系,君主在危难时应有的作为,权臣对国家的应有态度,甚且士人在国难时的出处大节皆清楚表出。这是他作为一介儒生在明清之际的主要时候对明亡的反省,对未来文化、政治诸大事的建白。一个欲以学术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存心于此灼然可见。
【文章摘选】《第七届天下儒学大会论文集》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