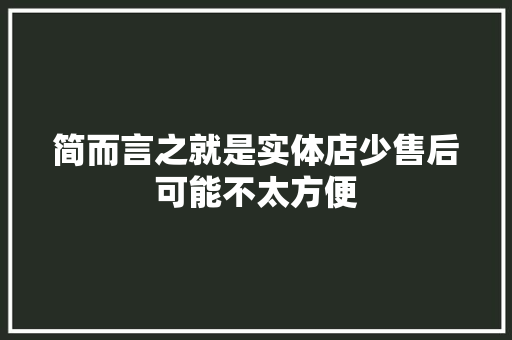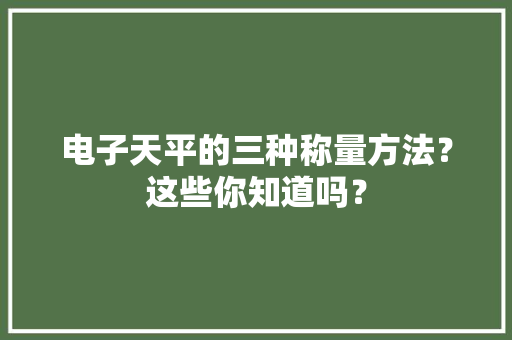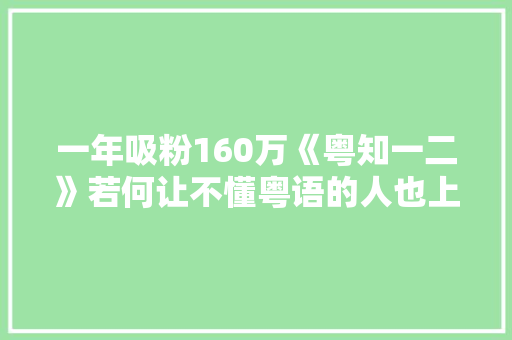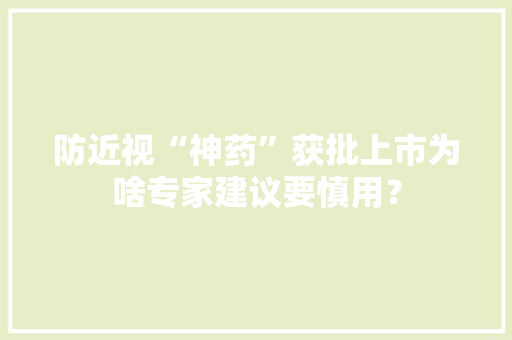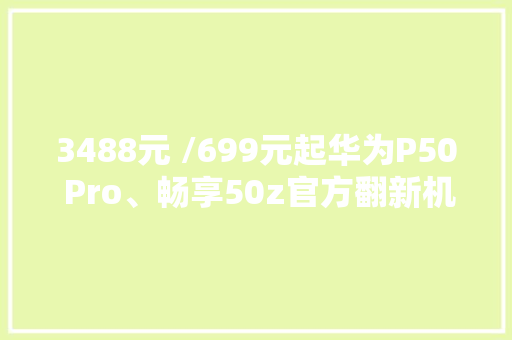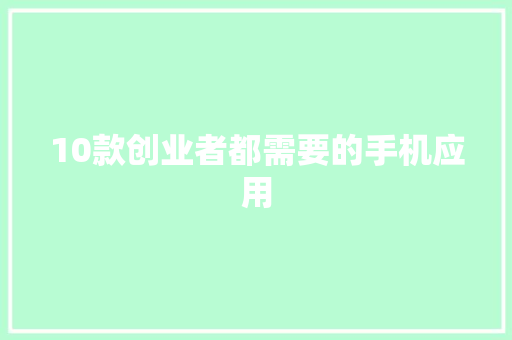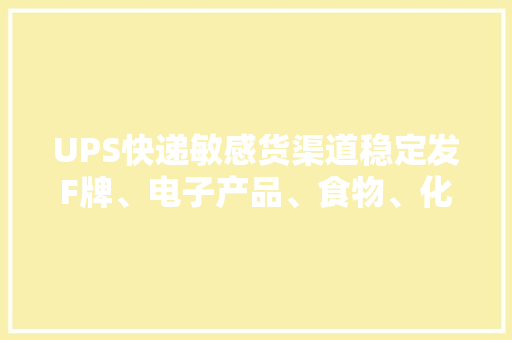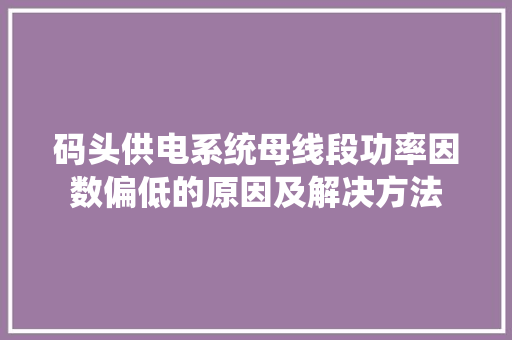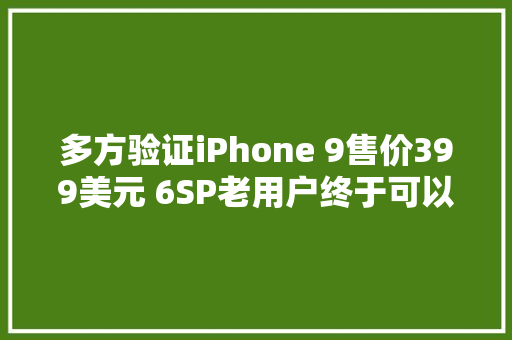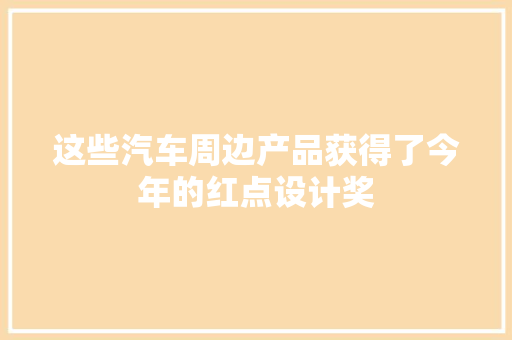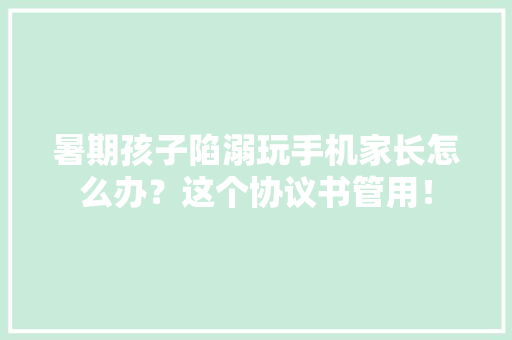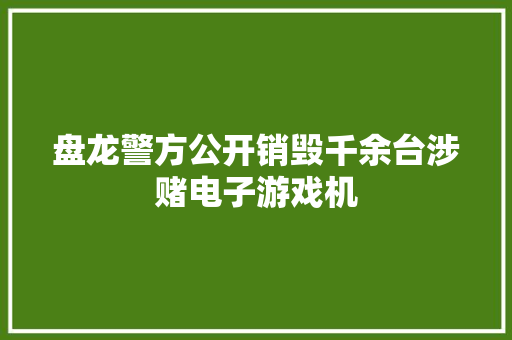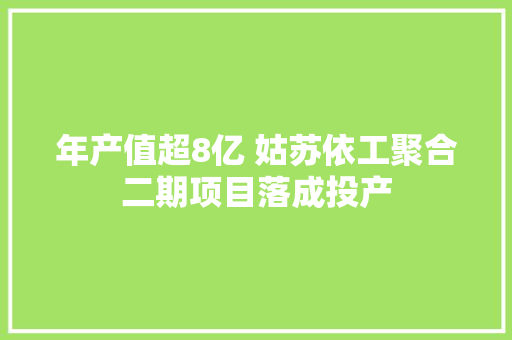“现在街上还有邮筒吗?”
“啊?不知道,没看到过。”快递小哥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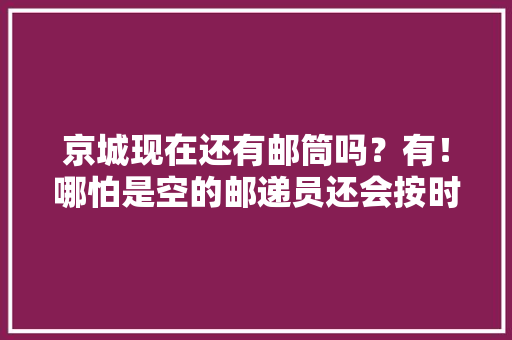
妻子也插话:“对啊,现在快递这么方便,还有邮筒吗?”

是啊,现在叫快递员上门,便捷又高效,谁还专门到邮局寄东西啊?不过,那曾风光一时,路上没隔多远就立一个的绿色邮简,真的只成了影象吗?于是,我从百度舆图上找了一个最近的邮局,要一探究竟。
从北苑路步辇儿向北,穿大街小巷,一起不雅观察,还真没瞥见一个邮筒。按导航路线来到了万科星园邮政支局,在大门的右侧,我要找的邮政信筒就立在那里。颜色还是熟习的邮政绿色,样子还是当年的样子,两个投寄口分别注有“本市”“外地”,下面写着两次开取韶光。除了二维码是新增的,其它都还是影象中的样子。
资料图片。
邮局的事情职员小杨见告我,社会需求减少了,这几年邮政信筒设置得比过去少了。虽然很多时候邮筒都是空的,但无论信件多少,邮递员都会按时开筒取件。为了证明,我又跑了西城区、海淀区的几个区域,所见如前。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唐代墨客杜甫《春望》中的诗句,可见信在当时是何等宝贵。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手写平信已不是唯一的通信手段,邮筒也会像许多东西一样被代替,就像“电报”“电话亭”“寻呼机”等,逐步在人们生活里消逝。但这些东西也见证了时期的发展,给一代代人留下许多回顾。
我人生写的第一封信,确切地说该当是一个稿件,便是通过邮筒寄出去的。我上高二时,见义勇为的女孩王继秀为保护公共财产捐躯了,被共青团中心付与“精良少先队员”称号。我代表青年学生在付与大会上发言,这篇发言稿又被县广播站播出了。因年少浮滑,我把稿子寄给了一家报社。贴上8分钱的邮票,亲手把信投进公社邮局的邮筒,亲眼看着邮递员把它取走。寄出的是一个稿子,也是我的梦想。从那时起,我每天愿望报社能寄给我复书,可那个稿子却石沉大海了。
第一封情书也是通过邮筒发出去的。刚参军从军的那几个月非常想家,寄托思乡之情的最好办法便是写信,我拿起笔给亲人、朋友、同学写了一封又一封书信,参军的喜悦,部队的温暖,战友的情意,演习的辛劳,思乡的深情,都是书信的内容。当然也思念梦中的那个她,于是我写了人生第一封情书,悄悄把信投进邮筒,不多久,在期盼中等来了复书。就这样,我和她一来一往通了近7年的信,她也终于成了我的妻子。
身为通信员,战友的信件大多是我亲手投进邮筒的。那时,我不只帮战友寄信,有时还帮战友写信,乃至还帮一位战友写过情书。自认为洋洋洒洒的表白,现在想来是多么稚子,想必看信的姑娘一定笑话写信的人了。唉,谁让我们那时候年轻呢!
一晃几十年过去,记不清多久没写信了。真怀念那些有书信来往的日子,在慢悠悠的光阴里,诚挚而从容地倾诉。想家了寄一片乡愁,想她了寄一番情思,有了成绩写给亲人分享,有了困难通过书信分忧。工余之后,夜深之时,展开洁白的信笺,将心扉打开,让思绪放飞,把所有感情的喜与忧,生活的苦与甜都倾注笔端,把问候、祝福、勉励、顾虑,写成一封封书信,然后将他或她的名字工致地写在信封上,郑重地投进绿色的邮筒。
绿色的邮筒如今看上去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里面装的大概不再是最急迫的互换需求,但它却依旧承载着俏丽的情绪,也会永久留在这一代人的影象里。
来日诰日出门的时候,大概你会留神大街上有没有绿色的邮筒,大概会勾起你一段美好的回顾。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陈广生
编辑:王琼
流程编辑: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