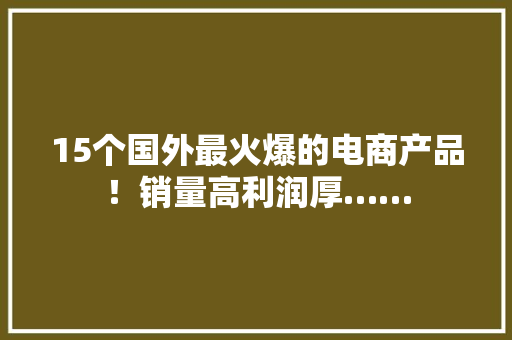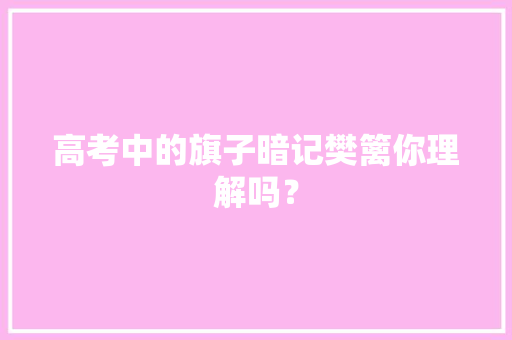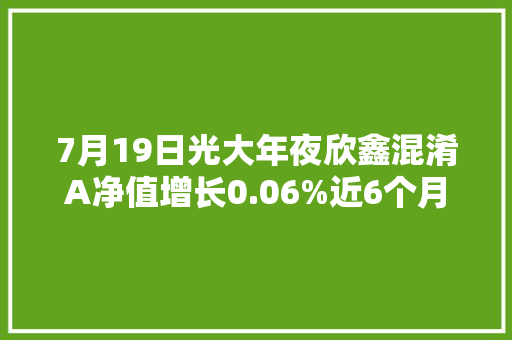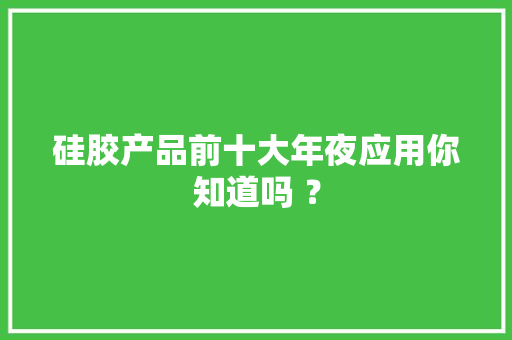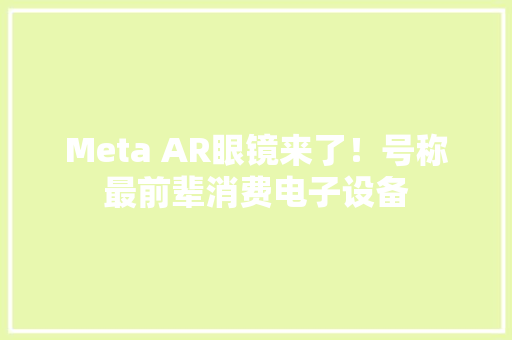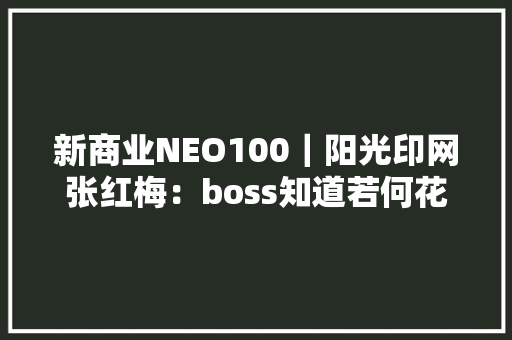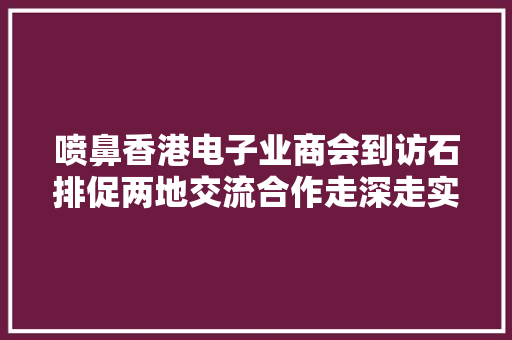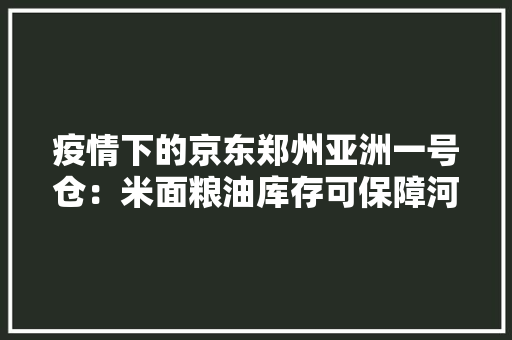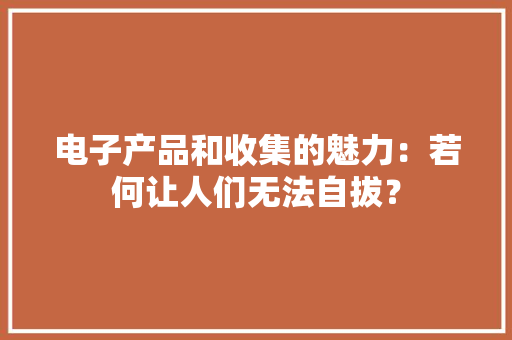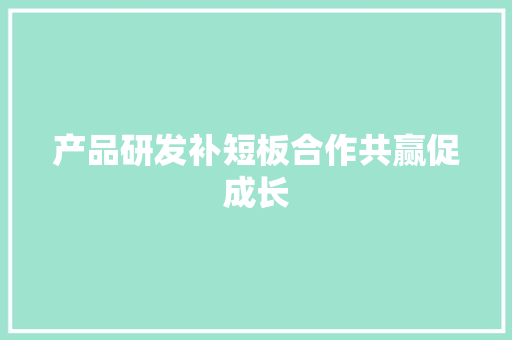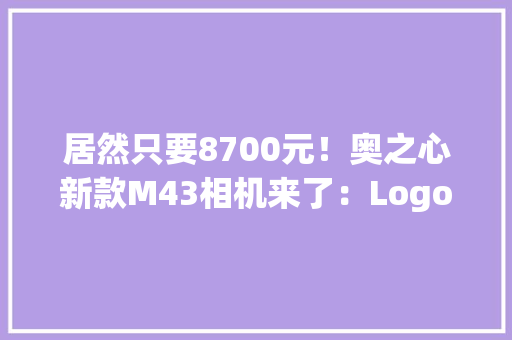熊彼特认为,创新作为新组合或者生产函数的变革,有五种基本的经济表现形式:开拓新产品,引入新过程,开辟新市场,掌握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后三种创新形式归入到新过程,由于它们也是改变了产品或者做事的供应办法。由此,我们就可以将创新分为两大类,即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
顾名思义,产品创新意味着涌现了新的产品,比如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推出了智好手机,或者是对既有产品有了质量改进,比如智好手机的不断升级换代。过程创新常日是由于企业通过“干中学”效应,积累了各种诀窍,优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比如太阳能板刚涌现时,每度电本钱很高,但随着韶光推移,干系企业积累了更多的技能知识,发电效率大幅提高了。同样达成一笔交易,以现金作为媒介要比原始的物物交流方便很多,而随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普遍利用,中国现在进入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无现金”社会。综合起来,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展、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生产本钱的不断低落,既是经济增长的推动机制,也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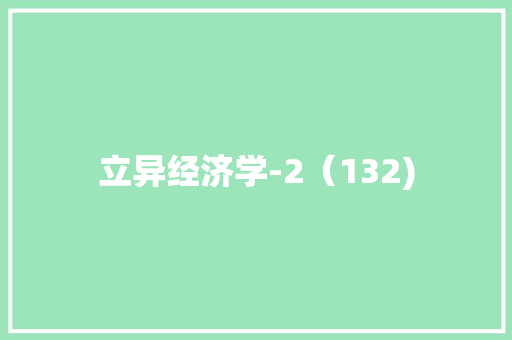
从投入产出的视角,产品创新表示能以相同的本钱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而过程创新表示能以更低的本钱生产出相同的产品。参照图14.1,左图展示了产品创新:需求曲线整体向外移动。产品创新意味着,对任何特定的产量q,市场对新产品的边际评价为p1(q),高于对老产品的评价p0(q)。右图则展示了过程创新:边际本钱曲线向下移动。给定需求曲线保持不变,单位产品的本钱从c0低落为c1。须要提醒的是,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很可能只是观点上的差异,在现实中两者每每很难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刚才提到的太阳能板的例子中,发电效率的整体提升固然可以算作过程创新,但能够实现这个结果,则是由于许多组件的性能提高了,即实现了产品创新。

图14.1: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14.1.2 创新的幅度
不同创新在新颖性上是有差异的。很自然地,人们将新颖性相对较低的创新称为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而将新颖性程度很高的创新称为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代步工具从马车变到汽车,对应的是颠覆式创新,而汽车涌现之后,其在车型和性能上的不断迭代和提升,则对应于渐进式创新。
熊彼特强调了颠覆式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浸染:“不管加总多少辆邮件马车,你都无法由此得到一条铁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渐进性创新对付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不主要,虽然每次变革都很细微,其不断改进的累积效果却是极其可不雅观的。正如前面数码相机的例子所解释的,绝大多数颠覆性创新刚涌现时,都会由于性能不稳定或者本钱过于高昂而缺少经济上的可行性。但在此根本上,经由发明者本身或其他后来者持续不断的渐进性创新,其性能会不断提高,本钱也不断低落,并终极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完备替代掉原有的产品或技能,进而实现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可以类似地理解创新与模拟的差别。从观点上讲,创新是产生了某种真正新颖的的东西,而模拟则是复制已经涌现的新技能或新产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创新和模拟(imitation)每每只是反响了新组合在新颖性程度上的差别,在性子界定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如何理解新技能从发达国家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征象?从发展中国家的局部视角看,这种技能在其经济社会中具有高度的新颖性(novelty),故将其引入和采取过程称为创新并不为过。但在环球范围内,这不过是新技能在空间上的扩散,因而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能模拟行为。
从市场竞争上风的视角看,创新者与模拟者也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创新者可能会由于前辈入市场而享有市场荣誉和先动上风,并有可能借助专利等知识产权构筑起制度化的进入壁垒。与之比较,模拟者则可能由于缺少与创新干系的知识、诀窍和工艺,不能完美复制出创新产品或流程。比如许多新药在专利保护期满之后,竞争企业所生产的仿制药也难以达到原研药的质量和疗效水平。
但情形并非一定如此,有时候模拟者反而会得到显著的后发上风。有了创新者的前车之鉴,模拟者更可能绕开一些技能陷阱,而随着韶光推移,公开表露的干系科技知识会越来越多,模拟者可以据此进行“周围创新”并绕首立异者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也能够更加适应要素供给或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形。根据Mansfield的估计,均匀而言,模拟本钱大概在创新本钱的六成旁边。一方面,这解释技能模拟本身本钱不菲,但另一方面也解释,模拟者的确享有巨大的本钱上风,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上风的主要来源。
14.1.3 创新的过程
创新本身是一个包括很多环节的繁芜过程。为了简化和方便剖析,经济学家常常将创新抽象为两个序贯环节—“研究”(Research)和“开拓”(Development),个中“研究”的浸染在于创造出产品或技能“蓝图”,而“开拓”的浸染在于将“蓝图”商业化。更进一步,“研究”又可细分为“根本研究”(basic research)和“运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前者侧重于创造没有明确的商业前景的科学技能事理,后者则致力于科学技能的现实运用,常日已经具有相比拟较明确的商业前景。
不过,正如创新与模拟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一样,根本研究与运用研究之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交叉领悟。最范例的例子便是三极管的发明。一方面,阐明清楚三极管的浸染事理具有巨大的科学原创代价,三位贡献者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另一方面,三极管也具有巨大的商业运用前景,为此贝尔实验室在申请了干系专利之后,才许可科学家们将其在学术杂志上公开拓表。
创新不是凭空涌现的。或多或少,任何创新都是在其前期创新根本上的完成的,同时又为其后续创新奠定了根本,这表示了创新的累积性。对此,牛顿有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由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结果。如果将研究与开拓分别算作不同的创新,则研究是开拓的先期创新,而开拓是研究的后续创新,而创新的积累性意味着,没有研究作为根本,开拓也就无从谈起。
详细到经济剖析中,我们可以按照累积性程度的差异,将创新分为离散创新(discrete innovation)和繁芜创新(complex innovation)。离散创新与其他创新的相互影响比较弱,故在经济剖析时可以忽略创新的累积性问题。与之比较,繁芜创新与其他创新有紧密的前向或者后向关联性,因而在经济学剖析时必须考虑创新的累积性问题。
繁芜创新的第一种主要的环境是集成创新,即某项创新的实现依赖于许多前期创新,因而具有很高的集成性。比如说,一种生物医药产品须要利用到多个基因片段的技能,或者某种电子产品须要利用到某种技能标准,而这种技能标准又是由许多专利技能共同组成的。
繁芜创新的第二种主要的环境是通用技能(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其构成了很多后续创新的前期创新,因而具有很高的通用性。蒸汽机和互联网都是个中范例的例子。蒸汽机发明之后,广泛利用并为各行各业供应动力,催生了工业革命。互联网极大地降落了人际之间的信息沟通本钱,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14.1.4 创新的模式
创新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一定受制于供求成分。与之对应,经济学家关于创新模式有两种基本的经济阐明,一种是强调供给面成分的科技推动说,另一种则是强调需求面成分的需求拉动说。
图14.2展示了科技推动说的基本逻辑。它将创新刻画为从根本研究到运用研究到开拓研究再莅临盆和发卖的线性过程,个中根本研究是全体创新过程的原动力。熊彼特强调了颠覆性创新的主要性,可以认为是此种理论的思想先驱。从观点上理解,颠覆性创新都是与某种新技能干系联的,在其涌现之前,绝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对其完备没有认知。比如,在乔布斯和苹果推出iPhone之前,市场所熟习的是由诺基亚所首创的功能机,但iPhone一旦推出,智能机就自动地创造了市场需求。
图14.2:科技发展推动创新活动
与科技推动说干系,对科技政策制订以及科技进步本身影响极其巨大的是一份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在“二战” 欧洲沙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斯福总统致信时任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Wannevar Bush),哀求其对如何把战时的科学技能履历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提出建议,其结果便是这份政策报告。
《科学:无尽的前沿》揭橥之后,不但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回响,成为无数研究、报告、剖析、阐明和评论的主题,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于天下各国的科技政策制订。报告将研究分为根本研究和运用研究,并强调了根本研究的至关主要性。
报告认为,根本研究会带来新知识。它供应的是科学成本,是所有实际知识运用的源头活水。统统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成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事理和科学观点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事理和科学观点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科学的进步一旦运用于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岗位、更高的人为、更短的劳作、更丰富的农作物,人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隙用于娱乐、学习,可以抛弃啰嗦的生活,阔别长久以来的劳苦。科学的进步也将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使疾病得以预防或治疗,促进我们对有限资源的保护,并为抵御侵略供应更多保障。作为落脚点,报告提出政府应该承担起新的任务:促进新科学知识的呈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
如图14.3所示,关于创新模式的一种替代经济阐明是需求拉动说,个中创新过程是从市场需求到研究开拓再莅临盆和发卖而展开的。作为这种经济阐明的先声,恩格斯有一句精彩的论断:“社会一旦有技能上的须要,则这种须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提高。”如果说科技推动说认为科技进步的结果无法预期,那么,需求拉动说的倡导者则认为,在很多情形下人们能够比较明确地感知到创新产品或者做事的潜在需求。
图14.3:市场需求拉动创新活动
这种理论阐明兴起的历史背景是,在1950和1960年代,军事等行业领域的大量实践表明,许多技能成果来源于利用者的需求,而不是任何预先设定的科学想法。与此同时,在大公司中,计策方案部门的主要性快速提高,它们致力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市场研究来确定能够知足者需求的新科技,而计策方案部门之以是认为它们能够预测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据可得到性以及剖析方法进有了大发展,使得社会科学的预测力有了显著提高。
关于创新模式,上述两种理论要么只强调科技推动,要么只强调需求拉动,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图14.4所示,一个自然的拓展剖析便是将两种成分综合起来,由此就会得到关于创新原动力的推-拉理论,个中科技推动和需求拉动都可以成为不同情境下的创新原动力。参照前面按照创新幅度的分类,颠覆性创新会催生全新的技能轨道,其创新后果很难事前预测,有待事后逐渐创造和挖掘,因而更加符合科技推动说的阐明。但在新产品或者新流程涌现之后,对应于既定技能轨道的渐进性创新,即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以更好知足消费者需求,如何改进流程以进一步降落生产本钱,则比较有章可循,因而更加符合需求拉动说的阐明。
图14.4:创新活动的“推-拉”模式和生态系统
抛开科技推动说和需求拉动说之间的不同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不敷之处:将创新描述为一个单向展开的线性过程。
1970年代之后,诸多研究质疑了这种线性假设的合理性,由于现实不雅观察表明,创新各环节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反馈过程。不管是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来自用户和终极消费者的体验和建议都对付改进和优化研究活动都有特殊主要的参考代价。
比如,软件企业在推出正式版产品之前常日会先推出测试版(beta版),广泛征集用户和专家见地,以尽可能肃清个中存在的各种毛病(bug)。现在,许多企业不再试图追求一劳永逸式的完美产品,而是先形成一个“最简可行化产品”(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再以此为根本,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对产品或做事实现快速的迭代升级,以求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显著的动态上风。
进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期,传统意义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线变得日益模糊。互联网数字平台企业的运行是最范例的例子。一方面,它向潜在的买家和买家供应撮合交易的线上做事,但另一方面,买家和卖家的交易行为会被数字化并保留下来,由此积累形成的大数据又会成为平台企业进一步改进做事质量或者撮合效率的数据要素。
在图14.4中,我们将创新各环节框在一起,想表达的意思是各创新环节以及各环节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各种繁芜的反馈关系,因而创新活动的原动力不再大略地来自于某个特定方面,而这天益依赖于其所处的全体“创新生态”系统。
关于创新活动的微不雅观动力,熊彼特有两种版本的阐明。在其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阐明,即创新是由乐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所推动的。但三十年后,不雅观察到许多当代化的研究实验室纷纭建立并开始发挥主要浸染,熊彼特在后期代表作《成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强调了大企业中常规化、有组织创新努力的主要性。
考虑到很多企业家都是中小企业的创立者,而大企业常日具有较高的市场力量,故其早期阐明强调了中小企业对付创新活动的至关主要性,而后期阐明则意味着由大企业主导的垄断市场构造是比较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在此意义上,熊彼特的两种阐明彷佛是相互冲突的。
但从下面的剖析可以创造,透过这些表象上的差异,两种阐明有个一以贯之的内核,即“创造性毁坏”的动态竞争思想。创造性意味着,创新可以通过引入新组合而创造新兴的家当、财富和就业机会;毁坏性意味着,创新会冲破旧秩序,进而会毁坏一些既有的企业、产品、事情职位以及那些失落败企业的梦想。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对企业是死活攸关的事情,真正的竞争不是“在市场中竞争”(compete in the market),而是“为市场而竞争”(competefor the market)。来悛改组合的竞争,不管是表示为本钱上风还是质量上风,其目标不是在边际上侵消既有企业的利润,而是要从根本上革掉它们存在的根本,即要它们的命。
14.1.5 企业家精神
与创新密切干系的一个观点是企业家或者企业家精神。沿袭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干系论述,创新是由企业家所推动的,而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冲破常规以谋取逾额收益。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作为新组合或者生产函数的变革或者新思想付诸实践的运用过程的内在关联和异同之处。
在熊彼特的剖析框架中,常规(routine)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完备竞争的市场构造,个中所有企业都节制和利用类似的公开技能,因而相互之间的价格竞争导致每个企业都只能得到经济学意义上的零利润。须要强调,这个零利润是企业基于公开技能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结果。
推而广之,人们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所形成的各种干系“定式”,也正是反响了常规的含义。比如下中国象棋,面对“当头炮”,应之以“把马跳”便是任何棋手都熟知的下棋常规。从这个大略的譬喻可以理解常规的几个特色:其一,常规是在与某种普遍环境所对应的最优选择,由于应之以跳马,可以防止对方得到空头炮的显著上风。其二,常规操作每每不是并不是唯一的,由于面对当头炮,应之以飞相局也是行之有效的常规做法。其三,某种应对办法能够成为常规或者定式,表示博弈双方的局势是两分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由此得到显著的增量上风。
一旦将常规与零利润联系起来,企业家的独特浸染也随之凸显:通过冲破常规以谋取逾额利润,即得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利润。但是,到底如何理解这个逾额利润的来源或者实质呢?换个办法提问,假设不雅观察到某个企业凭借专利技能得到了不菲的在位垄断利润,这是否意味着它通过技能创新得到了逾额利润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得到专利技能每每须要巨额的研发投入,而且研发活动每每还具有很大的技能不愿定性,因而这个不菲的垄断利润可能只是巨额研发投入和技能不愿定性的合理补偿而已。
不妨考虑某个风险中性的企业F。假设它面临某个潜在的研发项目,如果投入I,则有的概率得到技能成功、申请专利保护并得到垄断利润P,同时有的概率v失落败,后续利润为0。与完备竞争市场的零利润常规比较,从事前角度看,只有vP>I时,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才可以得到正的预期利润,因而单看企业的在位利润不敷以判断其是否得到逾额利润。当然,按照一样平常的经济逻辑,给定企业是理性的,则只有预期到vP>I时,它才会进行该项研发活动。
但是,如果研发活动本身是竞争性的,即除了该企业之外,其他很多企业也能不雅观察到这个具有盈利前景的研发机会,它们将会就此展开专利竞赛,结果是将所有的逾额利润都耗散掉。某个企业要赢得专利竞赛,不但哀求它必须得到技能成功,而且是须要在其他企业之前得到技能成功,只有这样,它才能申请排他性的专利保护并由此得到垄断利润。直不雅观上理解,假设有n个对称的企业参与专利竞赛,每个企业都投入研发本钱I,并将每个企业取得技能成功并赢得专利保护的概率记为v(n),这该当是的减函数。以是,随着参与专利竞赛的企业数量n增加,每个企业的预期利润不断地低落。如果忽略n的整数约束,则由研发活动的自由进入条件可知,终极会有n个企业参与专利竞赛,并使得v(n)P=I,即参与专利竞赛终极只能得到零利润。
上述剖析表明,即便专利保护产生的垄断利润很高,竞争性的研发活动并不会产生逾额利润。此结论乍一看有点令人吃惊,但实际上并不奇怪,即便是研发活动,也该当屈服竞争导致租金耗散的一样平常经济学事理。完备竞争市场的条件条件是市场中有很多同质性的企业。对应到产品市场竞争,这种同质性意味着每个企业都能以相同的本钱构造生产相同的产品,而对应对研发竞争,则意味着它们不但拥有相同的资金本钱,而且要对研究与开拓的过程和前景拥有相同的预期和“认知能力”。既然完备竞争的实质在于浩瀚竞争企业之间的同质性,这反过来意味着,逾额收益一定由于存在某种形式的异质性缓解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首先是企业家在追求目标上的异质性。熊彼特从社会学角度刻画了“企业家”的独特之处。与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不同,企业家常日都有一些非经济目标的追求。
不妨引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企业家的特色描述:“他们的梦想和意志是创建一个私有王国,只管并非一定,其常日会延续成为一个王朝”;“他们有征服的意志,一种旨在战斗、旨在证明自己优于他人、旨在成功的冲动,而其所在乎的乃是成功本身,而非成功所带来的果实”;“他们会由于创造、将事情搞定、抑或只是开释了他们的能量和才智而乐在个中”。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辩证的结果:正由于企业家不完备追求经济利润,他们会做一些在普通人看起来“不划算”的事情,终极反而会得到普通人无法得到的逾额利润。
其次是企业家在认知能力上的异质性。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新组合”,但到底这个“新组合”到底新在何处?何以可能?又为何只能由企业家创造和引入呢?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行为人在认知能力上的有限性和差异性。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到,正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在任何时空状态,总有行为人“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情形存在;换言之,常日所谓的“最优化”,只是人们在既有认知范围内的最优化而已。
由此不难明得,一旦人们的认知范围拓展,选择集变大,原来的最优选择—前面所定义的常规—便不再是最优的,而在更大的选择集下的最优选择也就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更进一步,除了熊彼特所强调的那些社会属性,企业家的特质表示在他们比普通人更加具有洞见和远见,即更有可能在拓展选择集之中“创造”有利可图的“新组合”。
对付人际之间认知能力的差异性,《道德经》有句话做出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敷以为道。
举例解释,不妨将“道”理解为可以产生逾额收益的“新组合”—电子商务。企业家便是具有洞见和远见的得道之人,在线下大卖场还如日中天的二十多年前,就可以预见到电子商务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盛况。
勤而行之的“上士”好比是蔡崇信,听到企业家对电子商务所描述的美好愿景之后,立即辞去其在跨国公司的高管职位,以每月500块钱的薪水加入企业家的创业团队。“中士”的若存若亡,意味着他们对电子商务的美好前景将信将疑,因而在决策上犹豫未定。至于“下士”,则是更多的芸芸众生,在他们的人之中,电子商务完备是无稽之谈:站在卖家的视角,他们担心货发出去而收不到钱;站在买家的角度,他们担心钱付出去而收不到货。
点睛之笔是“不笑不敷以为道”,这与“股神”巴菲特探求代价洼地的投资理念是完备同等的,正由于芸芸众生以为电子商务是无稽之谈,与之干系的各种要素价格才会变得很低,进而才有可能产生企业家所追求的逾额收益。
经济学家伊曼努尔·柯兹纳认为企业家的特质在于对市场“套利机会”的“警觉性”。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从认知视角重新阐释常规和企业家的实质,也可以从套利视角理解柯兹纳式企业家与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差别所在。
简言之,常规代表了社会大众的认知,而企业家的特质在于他们具有洞见和远见,或者说高人一筹的认知,因而逾额利润在实质上源于人际之间的认知水平差异。
详细说来,与社会大众对生产函数—产品与要素之间对应关系的普遍认知相应,会形成与产品和要素相对应的均衡定价体系,则熊彼特式企业家的浸染是通过引入新组合—改变生产函数,构建一个新的定价体系,而两种定价体系之间的套利机会构成了逾额利润的源泉。
由于认知壁垒,熊彼特式企业家或者创新者在引入新组合之后,可以得到逾额利润,但随着韶光推移,越来越多的柯兹纳式企业家也会“创造”这种套利机会,进而会放弃原来的生产函数,并采取“新组合”,这便是常日所谓的模拟行为。终极,当足够多的行为人都节制了这种新组合,它也就变成了新的常规,而与之对应的逾额利润也会随之消逝。
综合起来看,熊彼特式企业家是通过引入新组合而制造市场的套利机会,他们代表了冲破常规,让市场走向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力量,而柯兹纳式企业家则是“创造”和利用这种套利机会,他们代表了规复常规,让市场向均衡的力量。
高炉矿渣变废为宝对此给出了生动鲜活的解释。高炉矿渣是炼铁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据宣布,2008年中国共产生高炉矿渣近3亿吨,并以每年10%旁边的速率增加。长期以来,堆积如山的高炉矿渣曾让不少钢铁企业头痛不已,不仅要占用大量的地皮,而且还会因扬尘和个中的重金属离子随雨水等浸出对大气、土壤和地下水系造成严重的污染。在经济学意义上,钢铁企业花价处置这些废渣相称于是乐意以负价格***终极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龙教授团队经由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节制了高炉矿渣超细粉大比例替代水泥熟料制备高性能混凝土的配比和方法等,终极将昔日的废弃物变成了市场上低本钱、高质量的“绿色水泥”,并被广泛运用于京沪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重点工程。以原来的技能水平作为参考点,矿渣的市场价格为负,而在新技能运用之后,矿渣变成了市场代价为正的“喷鼻香饽饽”,与这种价格差所对应的正是创新带来的逾额利润。但可以想象,随着“绿色水泥”大行其道,矿渣的定价将走向新的均衡水平,而当干系的知识产权保护届满之后,所有的逾额利润将随之消逝。
14.1.6 创新的外部性
与一样平常的经济活动比较,创新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给定创新本钱,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存在显著的差异,进而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失落灵。如果存在严重的可霸占性(appropriability)问题,即创新者无法全部霸占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创新活动就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进而会导致市场的创新投资不敷。反过来,如果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抢买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即从事创新活动的私人收益紧张来源于打劫了竞争对手的买卖,而不是创造了新的社会代价,则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进而会导致市场的创新投资过度。
创新或者研发活动不只是产生新产品或者新工艺,更是一个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只有节制了新的科学技能知识,才能产生“新组合”,实现“生产函数的变革”。与有形的产品比较,知识具有范例的公共品性子,即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
非竞争性意味着,一旦知识已经创造出来,增加利用者数量不会额外增加社会本钱,或者增加知识的利用者并不会降落其他利用者的所得效用。比如说,爱因斯坦证明了质能方程之后,其他物理学家也节制质能方程并不会增加额外的证明本钱,爱因斯坦将质能方程传授给其他人也并不会导致爱因斯坦“忘掉”质能方程。
非排他性意味着,新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创新者就很难阻挡其他人也得到新知识。比如说,化学药品一旦生产出来,可能很随意马虎被竞争者通过“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而知道干系配方;类似地,软件企业以光盘形式将软件产品***之后,每每很难阻挡其在更大的范围内的复制和传播。
须要指出,非竞争性是创新知识所固有的技能特性,但非排他性则会受到企业策略或者法律制度的影响。比如说,软件企业可以通过加密技能或者将软件做事与特定电脑绑定的办法来避免无本钱复制,而如果企业申请了专利保护,其他企业即便节制了创新技能,在没有征得专利持有者容许的情形下,也不能利用该技能。
创新知识的公共品性子是导致可霸占性问题和市场失落灵的主要缘故原由。根据非竞争性,只管得到创新知识须要很大的固定本钱投资(比如编写和调试软件代码的本钱很高),但利用创新知识的边际本钱很低(比如软件拷贝的本钱险些为零),故从事后即创新完成之后的角度看,社会最优哀求创新产品定价即是边际本钱,即将产品价格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如果这样,从事前的角度看,创新者将无法收回创新本钱,进而也就没有创新的积极性了。
进一步,如果创新者无法通过技能或者制度手段肃清非排他性,创新活动将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即便其他企业或者个人会利用该创新知识产生了新的社会代价,该创新者也无法从中获利,由此导致创新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可霸占性问题,而创新者的创新投资也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但是,即便没有真实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活动也会面临可霸占性问题。
首先,最直不雅观的环境是企业创新会增加消费者剩余。根据定义,社会福利即是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故在离散创新的情形下,如果消费者剩余增加了,则一定意味着创新企业没有完备霸占创新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比方说,创新企业推出了一种全新产品,不同消费者对其评价不同,但由于无法确知每个消费者的详细评价或者无法阻挡消费者之间的套利行为,企业无法对他们进行完美的价格歧视,而只能采纳统一的垄断定价,故在创新发生之后,那些评价高于垄断定价的消费者就得到了正的消费者剩余。
其次,企业创新可能会仅仅通过影响市场价格而产生所谓的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比如说市场中有两个企业A和B,不妨将它们的产品也称为A和B,一开始定价分别为Pa和Pb。现在,企业A实现了工艺创新,并将将价格降落到pa'。随意马虎理解,如果产品A和B是互补品,则A产品贬价会提高B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利润,即企业A的贬价行为对企业B产生了正外部性;反之,如果两种产品是替代品,则A产品贬价就会降落B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利润,即企业A的贬价行为对企业B产生了负外部性。之以是将上述影响称为货币外部性,是由于企业A的创新行为没有对企业B产生技能知识溢出,而只是通过价格体系而对企业B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