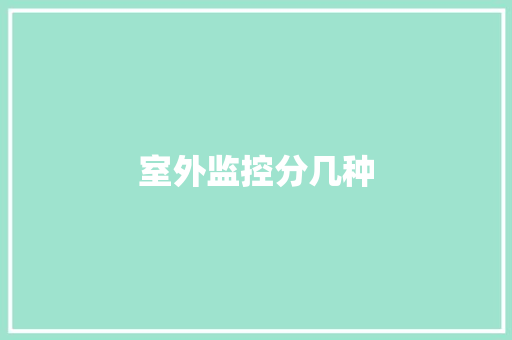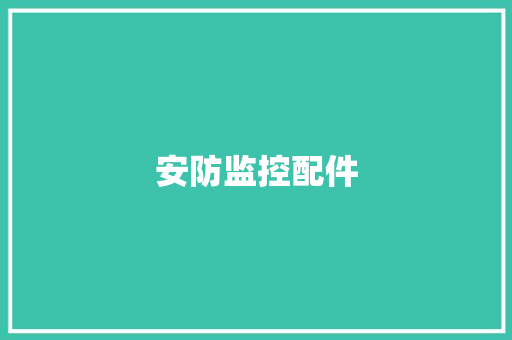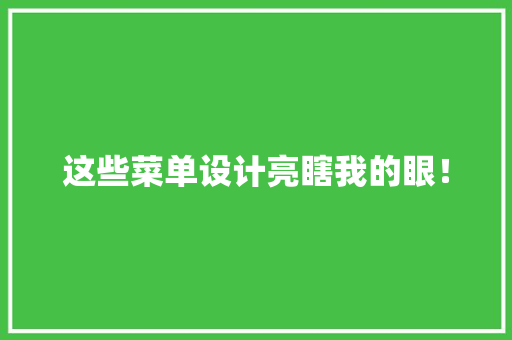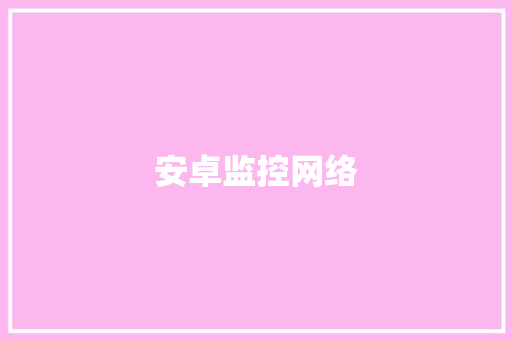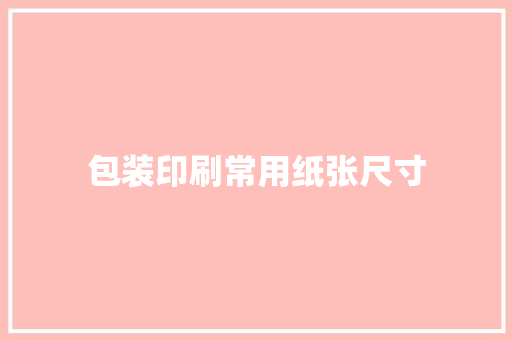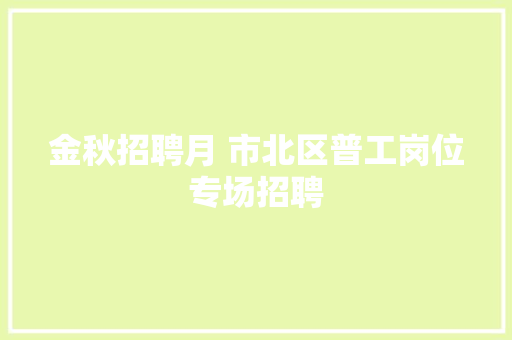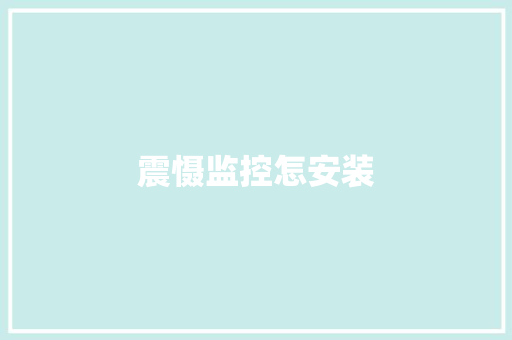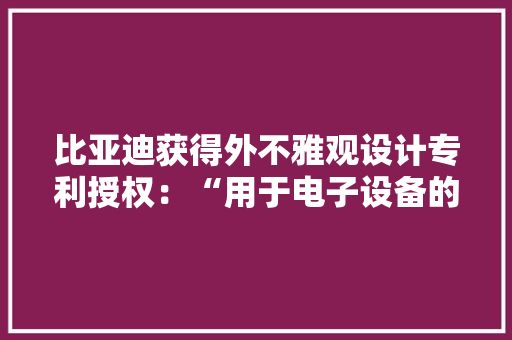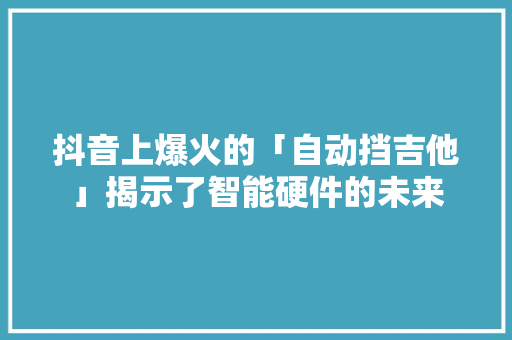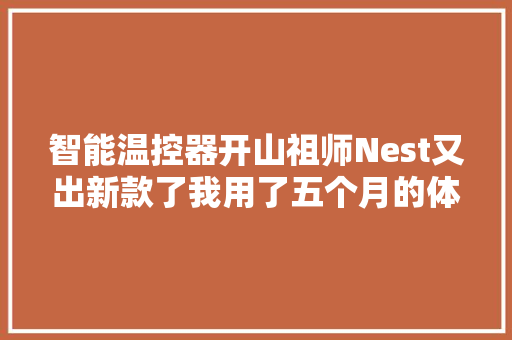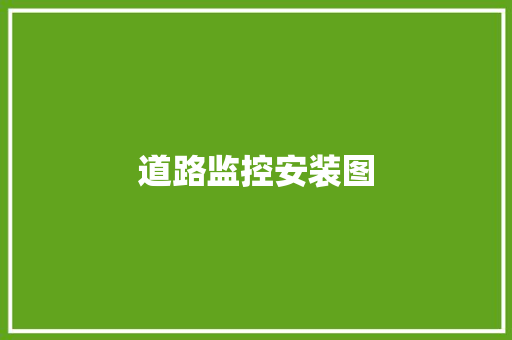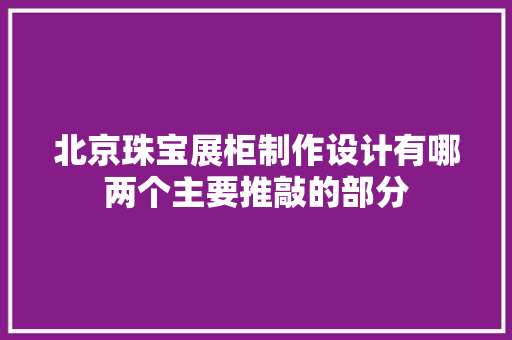确实现在时期不同了,对孩子、对家长的哀求也不一样了,没有可比性,实在父母也完备没必要心怀愧疚。在我的心目中,和同龄人比较,父母对我学习的关注已经算多的了。
我是70后,小时候,国家刚刚实施改革开放,还处处残留着操持经济的印迹,资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刚开始没有电视,后来家里有了一台14寸“莺歌”牌的黑白电视机,后来又有一台“燕舞”牌双卡收录机,这便是我当时眼中的名牌。到了晚上,电视中才会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台可以看,书基本上就成了我们理解表面的天下的唯一窗口。虽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父母仍旧尽自己所能为我们创造了最丰富的精神家园。记得每年年底时,父亲就会从单位借来邮局的订阅黄页,厚厚的一沓,各种刊物分门别类,让我们兄妹几人挑选想要订阅的书刊杂志,电视报、故事会、少年文艺、讽刺与诙谐,还有今古传奇、知音、青年文摘……都是我们家中的常客。平时,偶尔我们也会到新华书店挑选自己想要的书,后来再大一些往后,也试着啃一啃古典四大名著,还有《飘》、《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等一些外国名著,有自己买的,也有借的,也不知道看懂了没有。以是从小闲书倒是看过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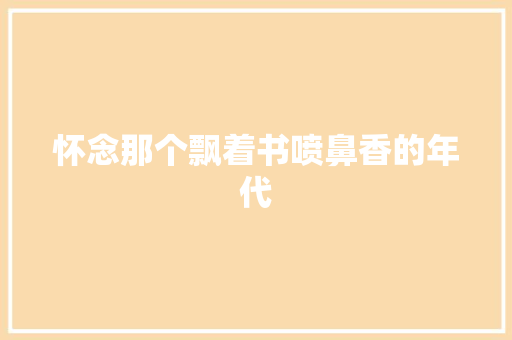
父母虽然没有太多的韶光顾及我们的学习,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时候父亲总会给我一个手掌大小的塑料套软皮本,让我写日记,那个小本本切实其实便是我童年的噩梦。有时候为了拼凑出一篇日记来,会把家里订阅的那些书猖獗地翻阅,探求写作的灵感,或借鉴或抄袭。那时候毕竟贪玩,年纪小也没有太多对生活的感悟,哪有那么多事情可写呀,每次好不容易挤一点出来,也是干巴巴的那几句话。更恐怖的是,父亲那时候常常下乡出差,等到他一回来就会检讨我的日记,这时候我才会创造大事不好,已经很多天忘写日记了,要补也不是件随意马虎的事,那个痛楚纠结,不说了。以是,小时候我特殊倾慕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只要写完学校支配的作业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的家长是绝不会有额外的任务的。不过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痛楚归痛楚,但这些经历或许多多少少对我还是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时期写作文彷佛没碰着太大的障碍,事情往后,无意中写了个单位报告前辈的材料就被领导创造我文笔还不错,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赏识,常常安排我写一些大大小小的申报请示材料、领导的讲话发言稿、单位的年终总结之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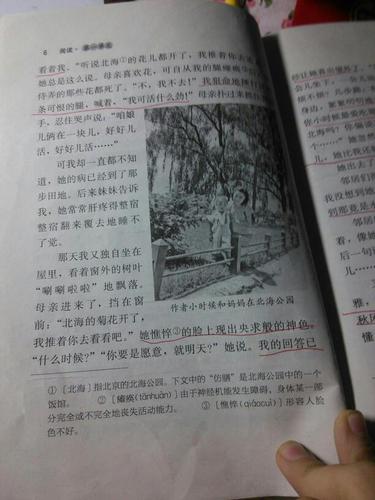
虽然小时候读过的书大多都忘了,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吃过很多好吃的食品,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难怪说“你的气质里藏着读过的书”。遗憾的是,现在在这个被各种电子产品充斥的年代,每天都流连于手机上的各种信息碎片中,彷佛难以静下心来去读一本好书,怀念以前那个飘着书喷鼻香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