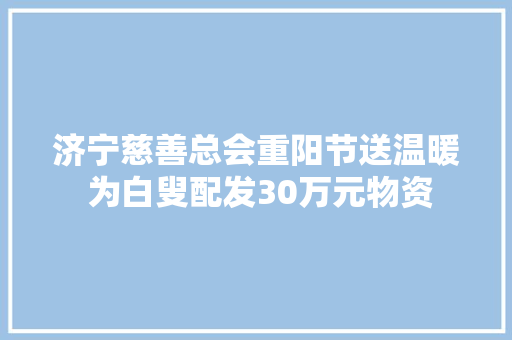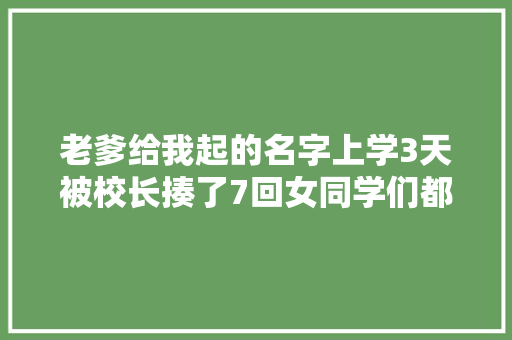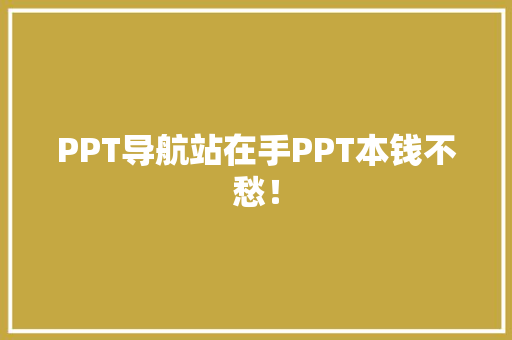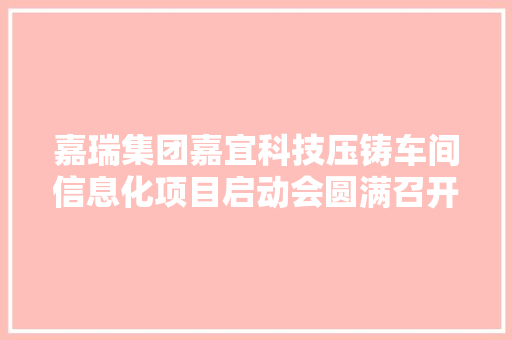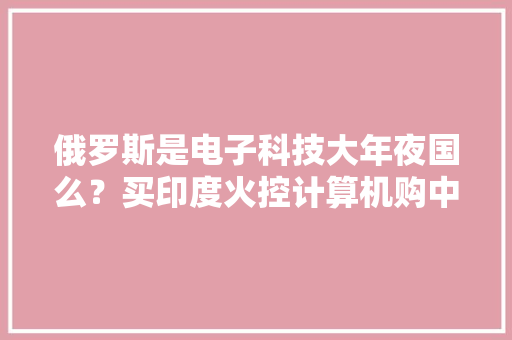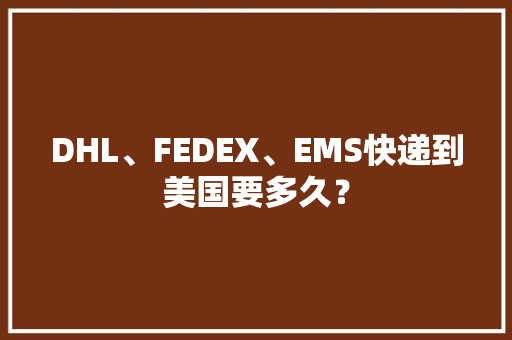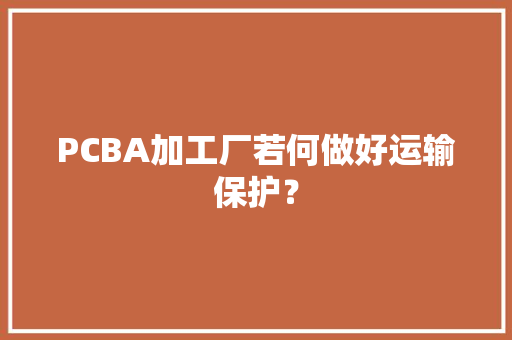几个月前,也便是1998年春,Konami游戏制作人大田良彦决定取消他和同事已经靠近完成开拓的一款格斗游戏。“在内心深处,无论我打算多少次,都无法想象这款游戏会脱销。”大田良彦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希望探求一个更让人愉快,更有首创性的创意。
街机曾经是电子游戏行业的命脉,但随着家用主机快速发展,街机行业陷入了低迷。市场在不断变革,如果游戏厂商连续大量炮制相同的内容,将很难知足玩家的需求。

大田良彦从自己放工后常常逛的歌舞厅找到了灵感。没过多久,他就带领一支由35名核心开拓职员组成的团队,动手为Konami首款仿照DJ节奏游戏《狂热节拍》(Beatmania)创作精神续作。《狂热节拍》在不到一年前问世,Konami的音乐游戏部门被命名为Bemani,开拓团队约请了许多职业舞者,并利用动作捕捉技能将动作分解为数据点。据大田说,他们通过“让程序员阅读一本舞蹈书”的办法,终极确立了《DDR》的基本玩法——开拓团队没人知道怎么舞蹈。

在《DDR》这款游戏中,玩家的嬉戏目标很大略。站在舞蹈毯上方,按照音乐节奏以及从屏幕下方往上涌现的箭头去踩对应的方向。
2007年,在《DDR》发售近十年后,墨客Cathy Park Hong出版了一部标题为《Dance Dance Revolution》的诗歌合集,以此向《DDR》系列致敬。Hong曾受《DDR》的启示写了一首诗,虽然后来并没有揭橥,但她仍旧认为《DDR》的“文化迂回”与她的作品主题同等。“这款游戏的起源让我着迷。”Hong见告《墨客与作家》杂志,“日本人将西方舞蹈动作变成了一款电子游戏,之后游戏又回到西方,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二十年前,《DDR》彷佛勉励了人们探求表达自己的新办法。
昔时夜田展示《DDR》的创意提案后,他的一些同事和Konami高层提出了质疑:谁乐意在公开场合被羞辱?“确实,有人大概会在玩游戏时感到尴尬。”大田回答道,“可你难道不以为除了尴尬的感想熏染之外,人们也希望有机会秀出自我?”
德语中有这么一个单词“fremdschämen”,专门用来形容间接的尴尬,可以大略地译为“为你以为害臊”。但若是几个朋友在KTV里纵情高歌并沉醉个中,就算唱歌跑调,他们共同的尴尬感是否反而会升华为一种快乐呢?
1998年东京池袋某街机厅人们围不雅观DDR的场景
在世纪之交,玩《DDR》成了年轻人互换时肃清尴尬感的一种有效办法。1999年,一批《DDR》机器抵达南加州,我从越南移民到美国的兄弟当时正念高中,他在街机厅创造了那款游戏。之后他将《DDR》(PS移植版本)买回家,还从日本购买了舞蹈毯。每逢家庭聚会,我们就常常唱卡啦OK或者玩《DDR》……那一年我才7岁,但《DDR》让我在与伙伴们互换时不再束手束脚。
但在美国,《DDR》最初是在北加州湾区掀刮风行浪潮——富有影响力的DDR在线资源网站DDRFreak.com就在那里出身。1999年,在位于加州森尼韦尔的Golfland娱乐中央,伯克利加州大学学生Jason Ko和年轻的软件工程师Cynan de Leon创造了一台《DDR》机器。De Leon喜好节奏游戏,当他在旧金山日本城的一家电子游戏商店闲逛时,有时听到了《DDR》的音乐。
“我当时想,‘这只是随机的舞曲CD。’为什么会在电子游戏区涌现?后来我研究了这款游戏,以为它永久不可能进入美国市场。”De Leon回顾说。
让de Leon没想到的是,《DDR》迅速火遍美国,他和Ko每周五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开车去街机厅玩这款游戏,朋友圈子也变得越来越大了。“昔时夜家把稳到同一批人每周五晚上都来玩《DDR》时,更多的人也想试一试。”他见告我,“我们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鼓励他们来玩玩。这款游戏门槛很低,你只须要战胜尴尬就行了。”
《DDR》富有吸引力,很随意马虎让人产生参与个中的冲动。
“当你看到《DDR》就会想,‘这究竟是一款什么类型的游戏?’”de Leon说,“机器特殊大,有灯光、音乐,有人在踩垫子。某些人动作很夸年夜,但也有人真的在舞蹈。在街机厅里,音乐和灯光就让《DDR》显得分歧凡响,让你很想试一试,或者嘲笑那些看上去动作很不折衷的人。”
许多电子游戏让玩家躲避现实,但有多少游戏能够让玩家在现实天下体验另一种身份?去年,曾为英国摇滚乐队电台司令(Radiohead)、说唱歌手Young Thug 制作音乐视频的Oscar Hudon推出了一部叫《高下旁边》(UpDownLeftRight)的短电影,讲述了一个日本上班族在一台《DDR》机器上快乐舞蹈被偷拍后成名的故事。
“如果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我不会舞蹈。”被称为“DDR之神”的电影主角说,“我须要人们的关注,如果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今年10月,媒体报导称一部得到Konami授权的《DDR》电影正在制作中,不雅观众们“将探索一个濒临毁灭边缘的天下,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舞蹈的通用措辞联络起来”。这个剧情设定让人以为挺无脑的,缘故原由之一是它照抄了某部拍摄于2011年,预算仅300美元的大学生电影((《Dance Dance Revolution: The Warrior's Path》)的关键情节。
不过另一方面,《DDR》确实能引发人们对人类与科技之间关系的思考。《DDR》于1998年9月尾在日本发售,同年8月,美联社揭橥了一篇标题为《500天修复千年虫Bug》的文章,谈到打算机有可能在世纪之交对日期识别出错,以及这件事的潜在后果。有人担心电网故障可能导致大范围停电,金融市场崩溃,全体国家的武器系统陷入瘫痪……
当人们从宏不雅观层面思考科技,就像在非母语环境中做梦,每每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过度担忧。1998年,许多人担心短视的科技创新将会闭幕人类文明,但《DDR》(从动手开拓到落成只花了4个月韶光)却为人们供应了一种循规蹈矩探索未来的工具。
机器拥有内部逻辑,并且每每比人类更稳定。我们创造机器来拓展人与人的沟通,但我们与机器之间又有哪些沟通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DDR》并不教玩家若何舞蹈,而是会发送专门的数字措辞,刺激人们做出特定动作。这就像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奇怪对话——虽然措辞完备不同,却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
在《DDR》风靡环球的同时,《雷神之锤》《反恐精英》和《暗黑毁坏神2》等游戏开始采取多人联网玩法,而这永久改变了许多玩家玩游戏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时至今日,《DDR》在电子游戏领域仍旧独一无二——《DDR》鼓励玩家活动身体,边嬉戏边演出,并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交场景。《DDR》为我们带来了虚拟现实,却又融于现实。
本文编译自:theringer.com
原文标题:《Are We Human, or Are We Dancer? The Legacy of ‘Dance Dance Revolution,’ 20 Years Later.》
原作者:Danny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