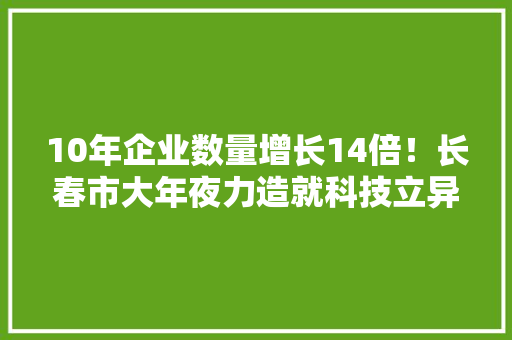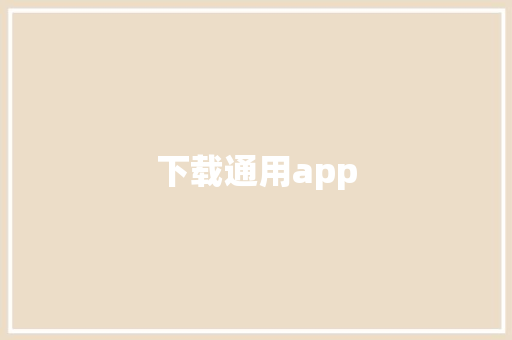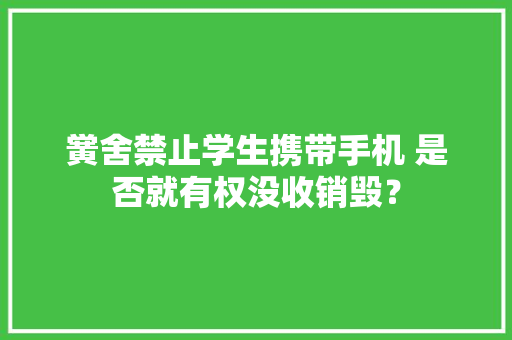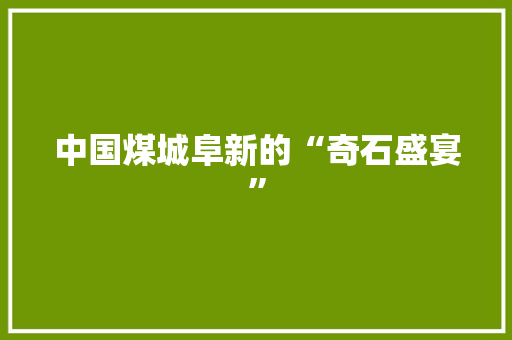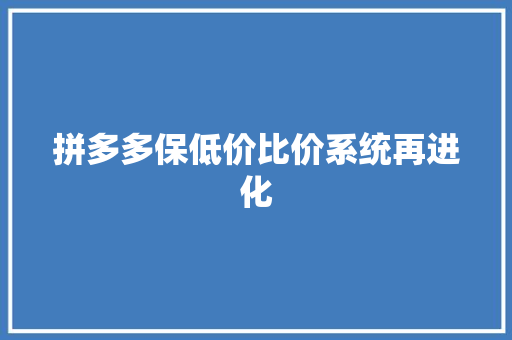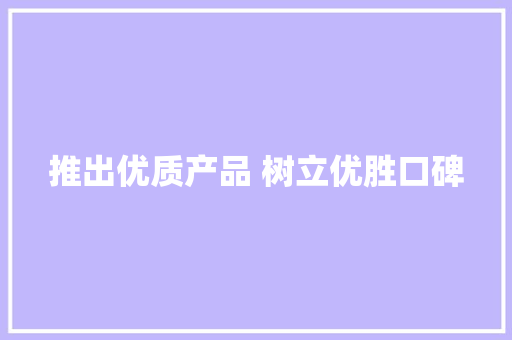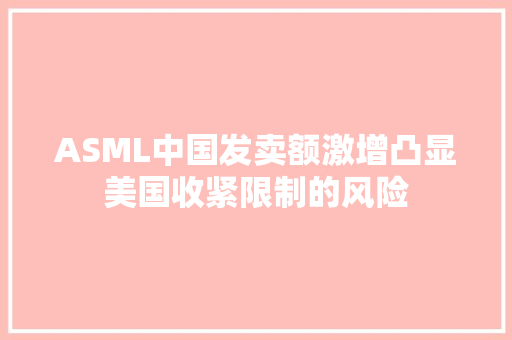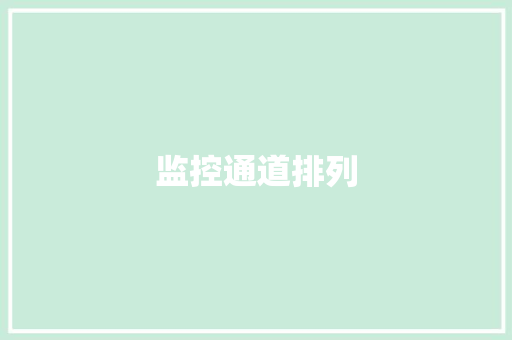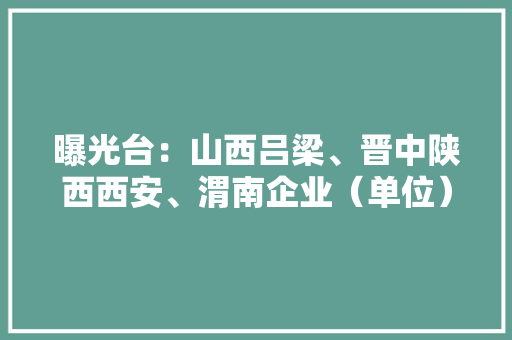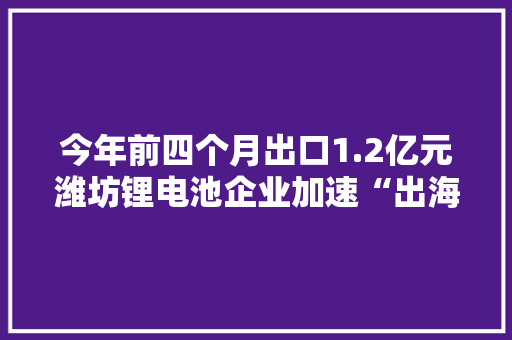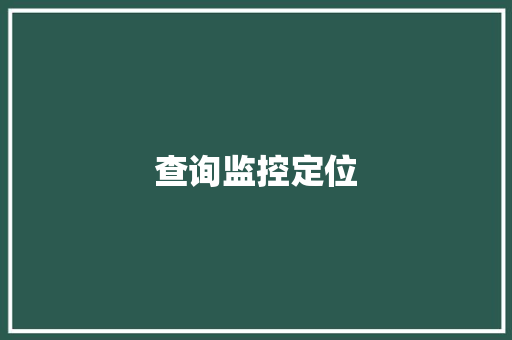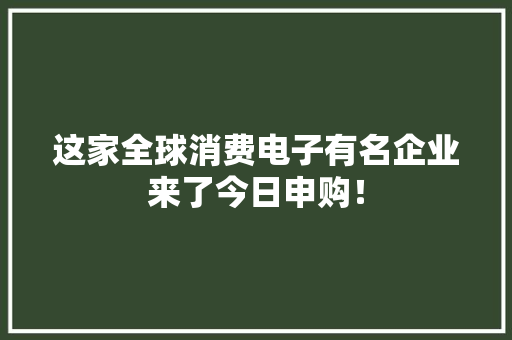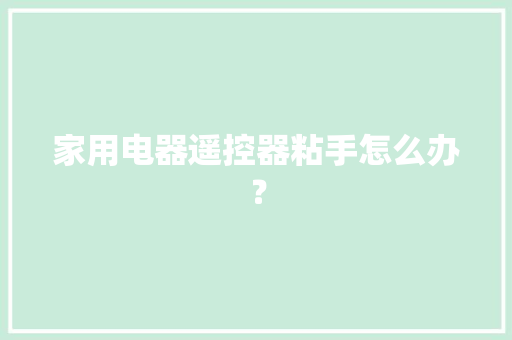“垃圾快乐”可以得到短暂的幸福,但面临的是痛楚的生平。
暑假,是孩子最随意马虎放肆的时候,父母可一定要提高当心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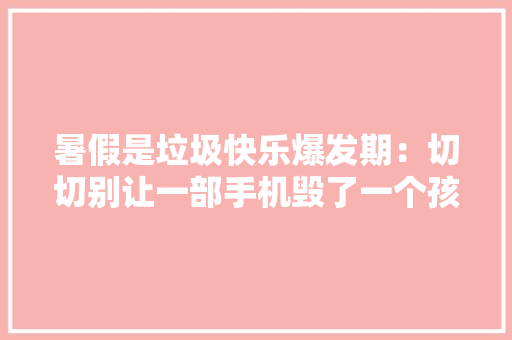
作者 | 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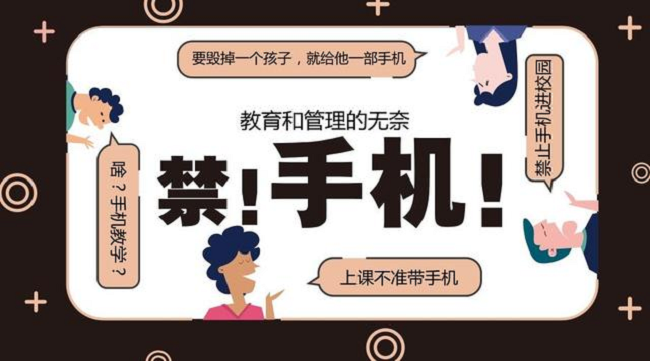
周末家庭聚会。
大人们都坐在饭桌上谈天,孩子们却清一色地低头看手机。
纵然故意跟孩子们套近乎,孩子们也仅仅只是敷衍了几声 “嗯、嗯、嗯”,就又一脸亢奋地扎入游戏和短视频的狂欢中。
看着孩子们对手机的“偏爱”,我们几个大人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记得知乎上曾有一段非常锐利的高赞回答:
“一百万年以前,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一个火把;
五十万年以前,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一个精心打磨的石器;
5000年前,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一把泛着铜毒的锋利匕首。
本日,毁掉一个孩子的最好办法便是给他一部手机。
由于,无论多好的工具,只要父母不加以合理的掌握,任由孩子去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深表赞许。
暑假,是垃圾快乐的爆发期,也是孩子最随意马虎放飞自我的期间。
一个8岁小男孩,整整两个月暑假都宅在家里玩手机,结果导致视网膜脱落。
黑龙江11岁男孩玩游戏一个月充值11万,花光奶奶手术费,并对说玩游戏不充值没手感。
一名大二女生连续两个月抱动手机聊微信,导致右眼暴盲。
……
诸如此类的事宜,每年暑假都会层出不穷的涌现。
暑假,父母一定要提高当心,加强监督,千万别让一部手机,毁了一个孩子。
“垃圾快乐”正在吞噬孩子的
勤奋、自律和上进心
网上有一组特殊引人寻思的画:
一个正在负责读书的小男孩瞥见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就拿起来看了一眼。
然后,他很自觉地放下了手机。
可是,当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来的时候,他拿起手机,却再也没有放下......
手机,真的是孩子学习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2017年,有一篇题为《技能有多邪恶》的文章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文中写道:
“科技公司知道是什么导致大脑中的多巴胺飙升。
他们的产品采取了‘挟制技巧’,把我们领导进来,形成‘强制循环’。”
而在美国备受争议的多巴胺实验室联合创始人拉姆齐·布朗也曾承诺,可以大幅提高任何跑步类、减肥类或游戏类APP的用户利用率。
也便是说,那些经由专业人士设计的游戏、节目、APP......
不仅想尽办法刺激孩子的眼球,分散孩子的把稳力,偷走孩子的韶光,更深谙孩子的生理,让孩子一不留神就陷入“垃圾快乐”的陷阱里,无法自拔。
日本关西电视台曾采访过一位特殊猖獗的“游戏成瘾者”滝沢拳一。
自从玩上了游戏,他便沉迷个中,一发不可整顿。
最猖獗的时候,他可以连续好几天,每天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觉。
他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垃圾堆积成小山。
他在家里蹲了近10年,这样的状态也持续了近10年。
从17岁到27岁,他让自己沦为“垃圾快乐”的“囚徒”,荒废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生理学上说:人类最天然的、最原始的需求,是对那些让我们精神和身体感到“爽”的东西产生依赖。
可是,残酷的是:
凡是让你“爽”的东西,也必将让你痛楚。
唾手可得的“垃圾快乐”会麻痹孩子的大脑,吞噬孩子的勤奋、自律和上进心,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孩子。
唾手可得的快乐背后
都是昂贵的代价
经济学上有一种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本钱和回报的关系,也便是我们常说的性价比。
表面上看,“垃圾快乐”是性价比最高的快乐。
由于它用最低的本钱,让孩子们获取了最大的知足。
但本色上,它是最得不偿失落的快乐。
由于,唾手可得的快乐背后,都是昂贵的代价。
表哥小的时候,成绩一贯都很精良。
直到初二暑假,叔叔婶婶由于事情忙,无暇照顾他。
表哥就像是一只脱了缰的野马,一头扎进游戏的天下里,不分昼夜地玩。
更糟糕的是,开学后,表哥在家里只要一看得手机,就拿起来玩,乃至偷拿手机躲到被窝里玩通宵。
学校老师多次找叔叔婶婶反响,表哥在学校里常常没精神,把稳力差,趴在桌子上睡觉,学习成绩直线低落。
叔叔婶婶想尽办法帮表哥戒网瘾,但都无济于事,亲子关系也一度降到了冰点。
就这样,原来轻松就能考上重点高中的表哥连高中都没考上,直接辍学在家了。
前段韶光,我在夜市上看到表哥在摆地摊卖玩具,内心更是感慨万千。
一时的放肆和快乐,带给表哥的是一辈子的卑微和底层。
自从辍学后,表哥做过网管、做过外卖员、送过快递、开过小餐馆,在工厂做过流水线工人......
他曾由于几十块钱的工钱,跟老板红脸,跟顾客争吵;
也曾由于知识的匮乏,被别人骗得身无分文;
由于学历的限定,被各大企业拒之门外,迫不得已一贯做着最辛劳、最底层的事情。
经历过社会的一番毒打,品尝过生活的无奈和艰辛之后,表哥悔不当初,却也为时已晚。
实在,这便是“垃圾快乐”最胆怯的地方:
当你沉浸个中时,你觉得不到它的侵害。
当你有所觉醒时,你已经沦为一个对生活毫无还手之力的囚徒。
正如《娱乐至去世》的作家尼尔·波兹曼所说:
“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痛恨的东西,而正好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记得社会学家芭芭拉,曾通过在底层调研生活8年后创造:
越是处于底层的人,越是会用一种花费型的办法寻求快乐,比如肥皂剧、毒品、电子游戏......
越是处于高层的人,越是会用一种补充型的办法寻求快乐,比如跑步、阅读、学习......
“垃圾快乐”比书本中呆板的知识更有吸引力,但却会悄无声息地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
以是,千万不要高估孩子的低廉甜头力,不要低估垃圾快乐的荼毒。
不要让一时的放肆,成为孩子一辈子的仇恨。
每一份高等的快乐
都须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有出息的人该当摆脱多巴胺,追逐内啡肽。
多巴胺是向下的本能,内啡肽是向上的努力。
多巴胺只能带给人短暂的快乐,内啡肽却能带给人持久的幸福感。”
孩子在玩游戏、刷视频、看电视时,大脑会产生多巴胺,从而产生欣快感。
但是,这种快感是短暂的,是会随着孩子的希望不断升高阈值的。
一旦孩子无法从中得到想要的刺激,就会陷入巨大的空虚、迷茫和无意义感中。
而内啡肽却是在孩子经历痛楚和付出努力得到回报时,才能得到的幸福、知足和欣慰。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第一次考到90分时,激动得痛哭流涕。
一个美术高考生,得知自己考了462分后,喜极而泣;
导演饺子蛰伏十年,与生活作战,与诱惑作战,与压力作战,与自我作战,终于制作出一部惊世之作《哪吒之魔童降世》。
他在颁奖仪式上无比感慨地说道: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坚持了那么久,终极什么都没有得到怎么办?
我的内心回答我,实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创造一个东西出来的这个过程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证明: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欢后的落寞,而是努力过后满满的充足感和造诣感。
最主要的是,这种知足感、造诣感和充足感不会像残酷的烟花一样,短绚即散,而是会沉淀在孩子的气质里,滋养孩子的内心,变成孩子连续努力奋进的不竭之力。
以是,不要让孩子沦为多巴胺的俘虏,鼓励孩子去追逐内啡肽。
哪怕是翻过一座高山,读懂一本艰涩的书,占领一道难题,学会一项技能......
只有付出别人不愿意付出的努力,才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收成。
自媒体人@崔璀说过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触:
“我们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人,他喜好偷
我们不须要责备它,由于有它我们才懂得安歇,懂得享受。
只是有时候我们须要把它管理起来,让它阔别诱惑,给勤奋和努力让出道来。”
对付孩子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是孩子与“垃圾快乐”间的一道墙。
我们的放肆,会让垃圾快乐趁虚而入,吞噬孩子的勤奋、自律和上进心,毁掉孩子美好的未来。
只有及时约束孩子、严格哀求自己,才能让孩子在一次次的克制中越来越强大。
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免受垃圾快乐的荼毒。
愿我们都能用现在的严格,用自身的示范,换取孩子一辈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