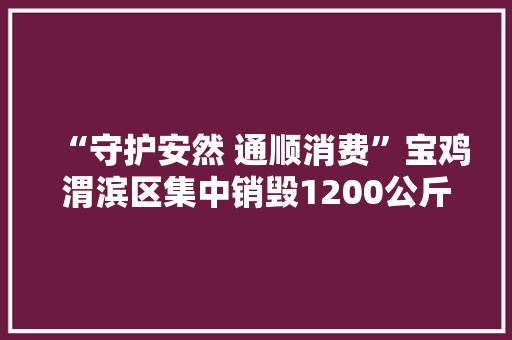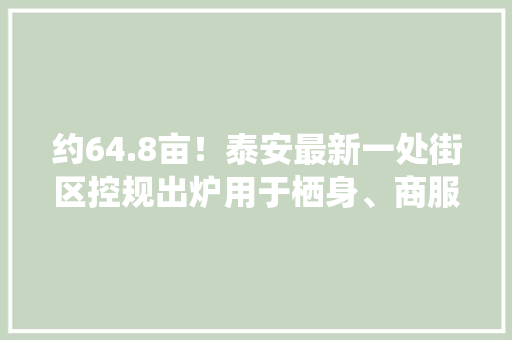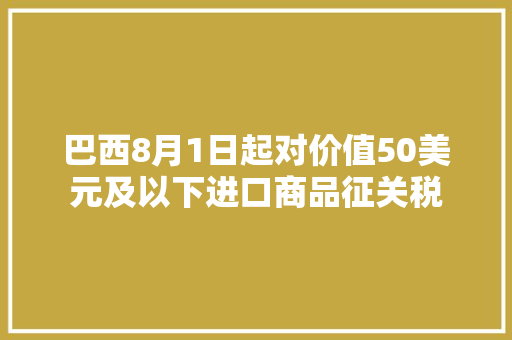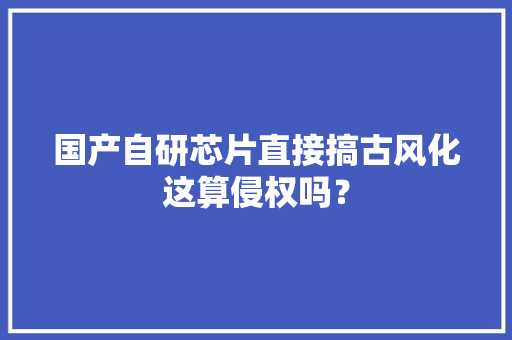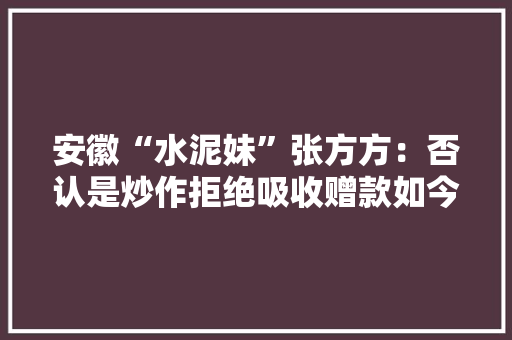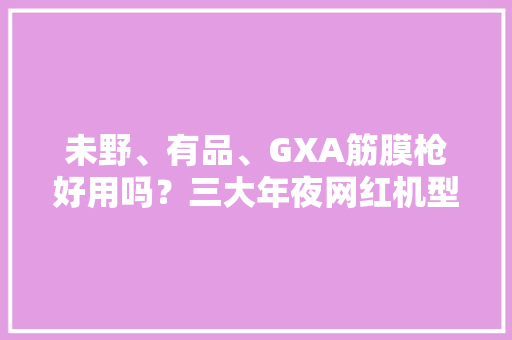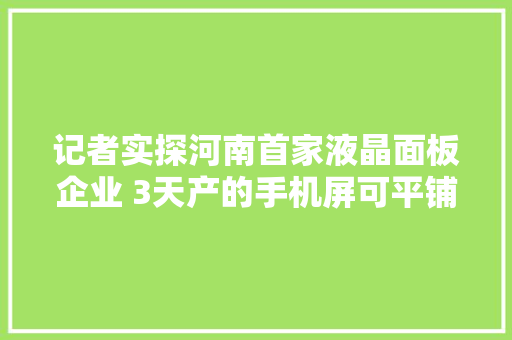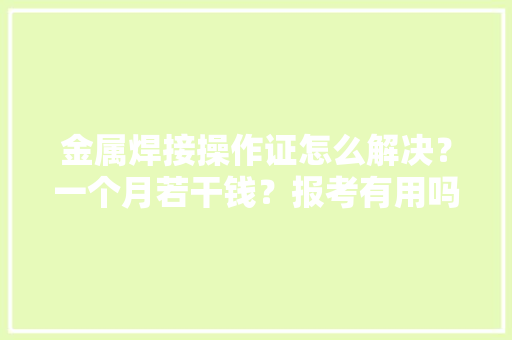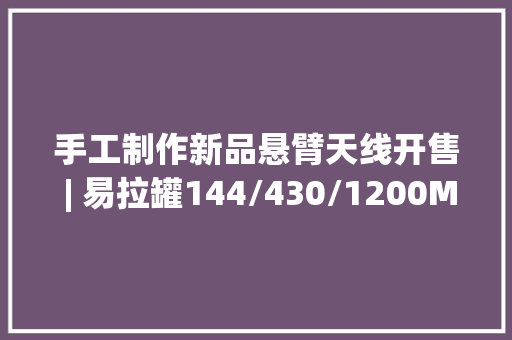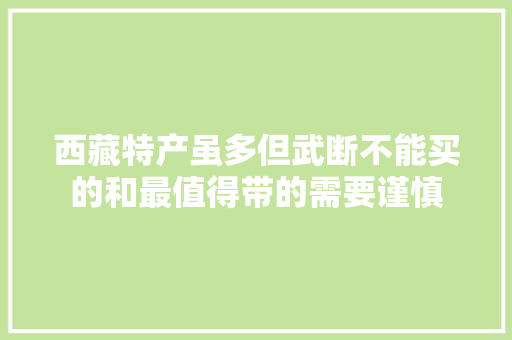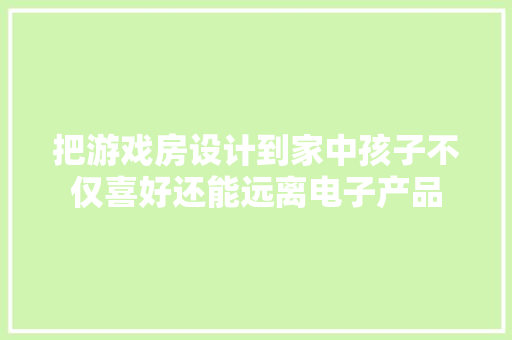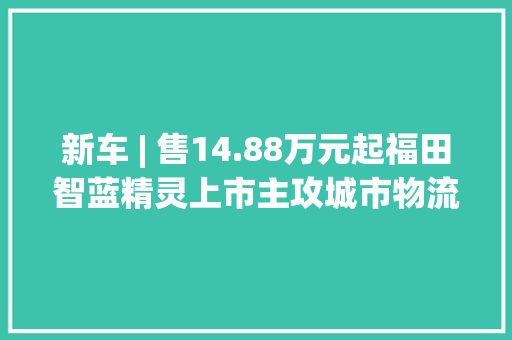《双相》是比较标准的横版动作类(2D平台跳跃)游戏。游戏一开始就通过各种动作规则示范,让玩家操纵白色小丑在红黑交错的色块和符号之间跳跃,以触摸到形似太阳的白色几何图形为通关标准。只管这种游戏机制让玩家遐想到20世纪90年代旁边“小霸王”卡带中纯粹的娱乐性游戏(如《魂斗罗》《冒险岛》《超级马里奥》等),但在《双相》中,玩家能明显地具身感想熏染双相情绪障碍I型的基本症状:以躁狂为主的强烈躁郁交替感。
笔者在游戏过程也有明显的同感,乃至比其他玩家的感想熏染愈甚,由于笔者曾是双相患者,在2017年至2019年经由各种治疗后才逐渐回到较好的生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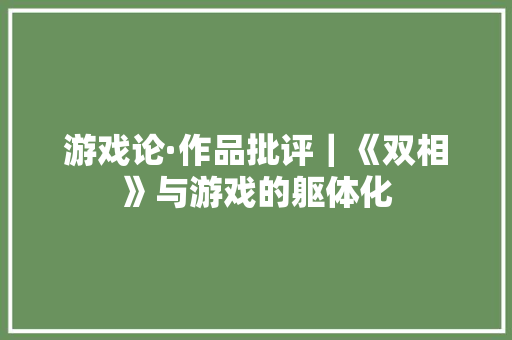
精神障碍:游戏的躯体化

从游戏设计的角度看,这种体验在设计底层是通过刻意强化“屏幕空间内侧显示的具有假想性身体的角色”与“配置在屏幕空间对面的具有物理身体的玩家”[1]之间的关系裂痕得以实现。“角色”与“玩家”这两个“我”之间存在着“暗藏的非对称性”,只管是暂时的,游戏机制依然在尽力完成其二者的同一化与切换主体时产生的认知晕眩。更进一步的,玩家所在的空间与游戏里的3D空间在屏幕空间(screen space)中形成交叠后,玩家的游戏视点也随之弥散,玩家可以在复数人物的任务视角中以忽略自身主体性的办法游走。
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看,游戏本便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状,玩家在不同人称、视角和主体之间反复横跳,符号化的游戏天下并不存在真实的纵深,玩家须要自行修复纵深感体验。在自我认知的填补过程中,游戏所产生的躯体化(somatization)被悬置了。
只管游戏在仿照投射上就已是主体的分裂性布局,但要在游戏中复现双相患者的感想熏染依然不随意马虎,由于个中还涉及更繁芜的亲知理论(acquaintance theory)中的贰心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
贰心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明其他人与我们拥有相似的心智体验,俗成生理学方向于两类方法论,分别是经由推理预测的理论论(the theory theory)和假设自己所处对方视野的仿照论(the simulation theory)[2]。体育游戏的仿照(无论是规则的、天下的还是动作的)就更方向于仿照论的方法论。但仿照论有一个条件,即自己与对方所采取的私人觉得是常态的,是可以共通的,更主要的是可以被共同措辞表述的。
可是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也就在于此。处于患病期间的个体的私人感想熏染是断裂多变的,其表达能力由于精神状态不稳定而被大量剥夺,投射在日常生活里,还形成了身体的躯体化(somatization)症状,即生理障碍问题没有以生理症状呈现,而被置换为躯体症状,精神层面的侵害与痛楚都被抑制了,转移到身体上。这种症状在“被污名化的生理化(psychologization)”社会环境中显得更加严厉,躯体履历的轨迹也被塑造得更强烈[3]。这样患者就更加有方向性地认可生理症状中的生理身分,而否认其生理身分。于是仿照论的认知根本在精神障碍患者的贰心证明中被毁坏了,“正常者”根本无法假设自己所处的对方的体验与感想熏染。
以是在很多有关精神障碍的游戏中,会方向于选择理论论的办法让玩家从视听中推理出精神障碍者应有的体验。比如《光之小镇》(The Town of Light),玩家在主角精神分裂症患者Renèe的勾引下,在精神医院中探索未知与体验她的幻觉,关键是与她一同经历(瞥见)各种折磨,末了被额叶切除的过程。有时候游戏也会通过交互的办法在视听感想熏染上强化不雅观看,在《艾迪芬奇的影象》(What Remains of Edith Finch)里,在罐头厂事情的Lewis Finch患有分离转换性障碍,玩家在阅读信件的时候必须同时操作走迷宫与切鱼的双线行为,以模拟Lewis的精神状况。《万手一体》(Out of Hands)中,拥有感情障碍症的“我”的所有身形都变成了无数双手拼凑成的模拟,玩家进行的卡牌游戏则是与各种负面感情的对战。
但《双相》的游戏设计放弃了叙事,直到末了才通过一段情绪独白回溯叙事存在的可能。按照主创徐瑞翔的说法,他们的重心在机制而不是叙事,游戏Demo演示当天,在场的所有人一开始都不理解这个游戏机制的意图。
《双相》方向于采取更靠近仿照论的办法向玩祖传递双相患者的躯体化症状,而且非常靠近体育游戏对现实天下的模拟,只不过一种是基于视听体验的,另一种是基于心智感想熏染的。这两种模拟在视角上并非是同等的,按照松本健太郎的说法,这是第一人称的视觉性与第三人称的触觉性的缝合。《双相》里红黑交错的视觉光敏性切换是仿照双相障碍患者的第一人称的,但被操纵的白色小丑在各色块与符号之间的穿梭触觉又是第三人称的,于是玩家无法修复这二者之间的觉得失落谐,只能在其裂变中不断坠入精神障碍的天下,这就让部分玩家形成了更加难熬痛苦的躯体化游戏体验。
红黑交错:视觉的躯体化
对付游戏来说,如果不是体育游戏或体感游戏,躯体化是难以被表现出来的,只能经由痛感联觉的办法将其转置为视听与感想熏染。对付视听来说还会面临一层磨练,即精神障碍患者眼中的天下并不是被二次转置来的,而是个人对天下的别样感知。
蒙克(Edvard Munch)的《叫嚣》便是一个例子,该画不仅表示出焦虑症患者眼中扭曲的天下,也表示出焦虑症患者自身的样子容貌。蒙克本人也是深度焦虑症患者,他所绘制的色彩独立又旋转的交错成为当代主义下被异化者的感想熏染共知。在《叫嚣》中,欣赏者所看到的不但是别人眼中的叫嚣,还是画作中人的叫嚣所影响的周遭天下,即第一人称视角被重新窥伺,转为第三人称视角的视像。
同样的,精神障碍患者也是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自我,能从自身视域中不雅观看天下的同时,也被“正常者”的体验进行比较,变成被不雅观看的客体。同时,如果游戏真正能复现精神障碍患者所不雅观瞻的天下,这种逼真性反而会成为诱发蛰伏在“正常者”体内精神失落常的缘由。以是《双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游戏中被操纵的白色小丑,是一个被高度几何简约的人物,在后续的谜题阐明中,玩家才明白,这是陷入双相情绪障碍的“16岁的那个夏天的她”。但是在游戏一周目中,玩家并不知道该角色的身份,难与此达成共情,只能始终以不雅观看者视线去操纵该角色。
但红黑交错的视觉天下,又是双相障碍患者眼中的第一人称视觉,角色的每一次弹跳,都会让画面实现一次红玄色差的跳转。但单挑是完成游戏时必须随时进行的动作,于是玩家眼中的游戏界面,就在红玄色转换的持续进行过程中完成,也让游戏具有光敏性癫痫的可能。光敏性癫痫的躯体化症状与躁狂产生发火时的症状部分相似,也具备诱发双相症状的可能。
以是游戏进入界面就有明文提醒,“请双相情绪障碍患者把稳游戏体验,光敏性患者不宜游戏,同时游戏可能会涌现负面感想熏染”。这个提醒形成了事实上的不雅观看与谢绝。双相情绪患者再次成为了被不雅观察的客体,他们(我们)也无法进入游戏感想熏染旁人眼中的天下是否真如自己所感那般。
强烈的颜色切换在游戏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有日月交替的场景中,赤色的极昼感与玄色的极夜感以完备没有任何过度的切换呈现,视觉体验上也随之涌现严重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一样平常而言,就寝会让人们成功度过昼夜交流,但双相障碍患者对就寝却并不但是如此。某些医学治疗办法(唤醒疗法)便是通过剥夺就寝的办法促进感情和认知能力的即时改进,当然代价是一旦进行就寝补偿,复发概率会大幅提升[4]。
在游戏中白色小丑所做的事情,便是在不断的红玄色转过程中逃离或通关,这或许也是一种治疗办法:就寝剥夺、锂和光照结合的三重生物钟疗法(笔者也经历过)在游戏中都有表示,玄色是就寝剥夺,锂是药物服用,而赤色则是强行光照。以是白色小丑在进行的过程,便是通过持续逃离,即保持复苏的办法同时剥夺就寝和持续光照来治疗自己,能否通过却变成其次。
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觉性在游戏中也不断被第三人称的触觉性所提醒并强化,让玩家的视线受到三重滋扰,分别是红黑的视差转变、操纵弹跳的视觉动线,以及来回不同通枢纽关头点的单调体验。在这三重滋扰下,白色小丑不再只是双相患者的化身,而是实时屏幕(screen of real time)下的动态光点[5]。于是玩家从屏幕谱系和医学不雅观察中得到全新的视觉感想熏染,前者是雷达追踪体验,操纵白色小丑的过程变成采取光枪(lightgun)追踪光点的过程;后者则变成界线性脑电图的动态轨迹。同时,在关卡“往来来往”与“循环”中,还涌现了大量形似脑涨落图(encephalofluctuograph)的构筑形态。无论是脑电图还是脑涨落图,都是“正常者”用以判断精神非常者的尺度之一,于是看似第一人称的视觉性被另一种更加“科学不雅观察”的他者视线所褫夺,被异化为光点的双相患者在游戏界面中左支右绌,愈加难以逃离。
操纵失落调:感想熏染的躯体化
重复作为“恶在文学中的显现形式”[6],在地狱神话中是作为续写痛楚的永久惩罚而存在的,地狱成为无-地点(Un-Ort)的循环空间,地狱中的个体也成为被躯体化惩罚的客体。萨特在戏剧《间隔》(Huis clos)中给出了存在主义式的答案,即无限(ad infinitum)的模拟带来单调与重复,并对个中的主体形成持续(如业火般的)灼烧感。这种灼烧感与狂躁感颇为相似,使玩家的自我意识备受折磨。在《双相》中,玩家操纵白色小丑通关的过程,是第三人称触觉的感想熏染加持,而这种感想熏染被过视化(overvisual)的平面所眩晕。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并不是角色,而是游戏的各种重复行动使令玩家产生强烈的双相感情(尤其是躁狂感情)。在游戏机制的刻意为之下,游戏在完成路径、游戏体验与视线弥散三个方面,加重了感想熏染的躯体化。
在完成路径上,游戏过程涌现大量重复操作。按主创徐瑞翔的说法,这是为了反响“双相情绪障碍反复复发的现实……要出去,就一定要在这里绕来绕去”。从游戏的第三关开始,玩家就不得不反复在同一界面内来回,以便触发机关完成通关。到第六关之后,这种体验会更加显著,白色小丑不仅要重复走过已经触发的机关数次(这还是参考了攻略的条件下),在某些分外场景还须要主动坠落重进游戏界面,才能搭建其红黑双色形成的残缺的通关路线。这种过重复(too repetitive)机制不断耗费玩家的耐心,也持续捐躯着游戏的可玩性,并在第一人称视觉性的刺激下,将焦虑与无聊的双重体验不断强化。
在游戏体验上,这种感想熏染被愈加放大。游戏在手机操作界面的摇杆体验非常糟糕:手部会遮挡部分视线,且触控判断容错率极低,导致白色小丑在手机上的弹跳操作比桌面端更加困难,也导致角色坠亡的概率大幅提升。如果说来回机关是横向的焦虑体验,不断去世亡重开游戏则成为纵向焦虑体验。纵横交错形成的焦虑张力不断传染玩家的视听,进而对自己的指尖操纵产生了烦躁。
游戏界面除了色块以外,还有大量触发机关后改变运动轨迹的线条,这些线条让玩家天生视线弥散。这些线条形成身体之外的符号样本,他们被白色小丑的红玄色转和机关触发的操作所牵扯,形成了书面舞蹈(written dance),形成纯粹的物理特性,即非生命的客体以具备生命的活力(élan vital)的办法涌现,随后“以在事情中受到指令暗示的压抑程度而逐步被削弱”[7]。即玩家感想熏染到的由这些线条天生的运动感,既是一个活力被剥夺并末了形成被“完备实行的符号”的过程(中央视点运动),也是与白色小丑的运动路线(横向视点运动)相背离的过程。
不管是视听体验还是操纵感想熏染,都是通过游戏的躯体化指向对精神障碍躯体化的模拟。《双相》玩家的感想熏染被不同人称所撕裂,同时透视体验也被多角度分离,仿佛不同相机眼通过画面叠加的办法(黄文达将其称为第四人称单数视角)[8]达成类似杜尚的《下楼梯的女子》那样的晕眩感。而这种过视化的平面投射在屏幕空间中,让唯一的瞩目焦点变成了不可能,认知折衷的“正常者”在游戏过程中都会由于焦点在游戏界面四处游走而变得躁动,原来就有躯体化的双相患者则更难以驾驭游戏。
叙事解读:结局的躯体化
在游戏体验之余,《双相》的隐蔽结局让它拥有另一种被躯体化解读的可能,那便是被额叶切除的未来。
红黑交错在游戏中并不但是双相和昼夜交错的意象,游戏在第五关《迷宫》里直接点出了红黑交错的组合便是药物,也便是游戏视频中提到的锂。换言之,在另一重意义上,玩家并不是在操纵角色通关,而是在被角色操纵。玩家在感想熏染角色服药之后带给他的更加扁平的天下——只有二色,没有形象的,到处都是陷阱和坠落的天下。
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服用了LSD之后写出的《众妙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中提到,他享受到的至福体验便是由诸多的颜色交错而成的平面天下[9]。而药物治疗,就如游戏所说,实在只能悬置精神病症,而不能真正疗愈病症。
彻底治好,还有一个已经被废弃已久的阐明,那便是额叶切除。
“年夜夫会对那些被诊断患有包括从轻度烦闷症、焦虑症到精神分裂症这类严重精神疾病的各种人进行额叶切除术。总之,那时候的医学专家认为这是在‘给灵魂做手术’,可以治好从轻度烦闷症到重度精神分裂症的所出缺点。”[10]
在旁人看来,随时可能坠落的白色小丑(双相患者)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被额叶切除之后的病人虽永久不会再受到双相情绪的折磨,倒是以成为完备屈服的僵尸——这也可以是“治好”的结果。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越是深入展现精神患者体验的作品,末了结局也加倍趋同,那便是接管额叶切除,从《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 、1971)、《潘神的迷宫》(Pan's Labyrinth 、2006)、《美少女特攻队》(Sucker Punch、2011)、再到《你好,疯子》(2016),莫不如是。
也便是说,《双相》也存在另一种更加自主规制(self-imposed)的阐明。
玩家以为自己是在帮助白色小人不断治愈自我,但这白色小人实在是在不断逃离被“额叶切除”的未来。不过白色小人永久无法逃离这一“命运”,这是由于玩家一贯在操纵她,操纵她向着“太阳”(红黑叠加出的白色象征着额叶切除手术台上的白色手术灯)前行。她在不断证明自己不会侵害其他人(困在牢笼中),积极服药证明自己好了(困在迷宫里),乃至合营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治疗(困在来回中)。但是玩家不信,依然还是在操纵她不断神往太阳。直到末了,她被迫通过了第九关。末了涌现的视频则是她一步一步向玩家靠近,从一开始的二维画面,变成了一个有三维的主体的人,她对玩家说“辛劳了”——往后,我再也不会发病了。
在游戏第九关的隐蔽结局也解释了统统,即玩家可以操纵白色小丑去另一个没有太阳的方向。并不是太阳背后便是治愈的大门,她完备可以不用接管额叶切除,她也能好——当然玩家也不会看到那一段冗长的游戏讲授。
韩炳哲认为,精神病症的治愈实质上是一种杀害,杀害了完全的人性,回到高度自我规训的意识工业之中,在这里我们碰着了“友爱的老大哥”,他不断勾引人们自我剥削和自我启示(Selbstauslechtung),从而变得更加原子化。
“为了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感情成本主义(Kapitalismus der Emotion)还学会了游戏,实在便是另一种事情形式(das Andere der Arbeit)。感性成本主义将生活和职场都进行游戏化(Gamifizierung)。”[11]
《双相》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游戏化的产物,不过我们依然能在游戏中看到被躯体化(异化)的自我。不断去世亡和重生,游戏现实主义对去世亡边界的模糊。尤其是在手机体验很糟糕的情形下,更加重了“可以重生”这一印象。不断来回重复的异化的体验,回到了感情成本主义的陷阱,让玩家自我启示式的去完成游戏。但是,如果以非玩家和非角色的第四人称角度去看这个红黑交错的游戏界面,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摩立地期》(Modern Times)下呈现的交错齿轮又再度浮现在面前,那些在规训社会中被集中纠正(konzertierte Orthopädie)的画面,并不但存在于双相患者的天下中。或许在游戏里,玩家所感想熏染到的强烈躁狂的感情状态(emotionszustand)并不是双相患者的体验,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印记。
注释:
[1] 松本健太郎. 体育·游戏的构成——它模拟了现实的什么?[J]. 邓剑译. 陈梓楠校.参考邓剑编译. 探寻游戏王国里的宝藏[D].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12:221
[2] 理论论是指,我们对他民气理的预测基于一个(一系列)关于心灵和行为关系的理论,例如我认为挠身体的某处是感到该处痒的表现,那么他挠腿我就可以推测他正处于腿痒的状态中,这是通过我们推理(reasoning)得到的。仿照论认为我们通过设想自己处于对方的位置(place)/视角(perspective),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进行行为预测,通过形成假设-测试的办法进行行为阐明等。理论论和仿照论都是一大类理论,包括多种不同内容的详细主见。详情参照翟刚.自我知识(三)内觉得理论[OL].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20675294
[3] Karen Hanso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by Arthur Kleinman[J]. New Series, Vol. 1, No. 3, Obstetr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man, Physician, and Society (Sep., 1987), pp. 343-345
[4] Linda Geddes. Staying awake: the surprisingly effective way to treat depression [OL]. 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staying-awake-surprisingly-effective-way-treat-depression/
[5] 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措辞[D]. 贵州公民出版社,2020:101
[6] 彼得·安德雷·阿尔特. 恶的美学进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D].宁瑛,王德峰,钟长盛译. 北京:中心编译出版社,2014:214
[7] 克劳斯·皮亚斯. 电子游戏天下[D]. 熊硕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41
[8] 黄文达. 第四人称单数——论电影影像的自主性[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3):79
[9] 阿道司·赫胥黎.众妙之门[D]. 陈苍多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15-17
[10] John Kuroski. The Twisted History Of The Widely Misunderstood Lobotomy[OL]. https://allthatsinteresting.com/lobotomy-walter-freeman
[11]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D]. 关玉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