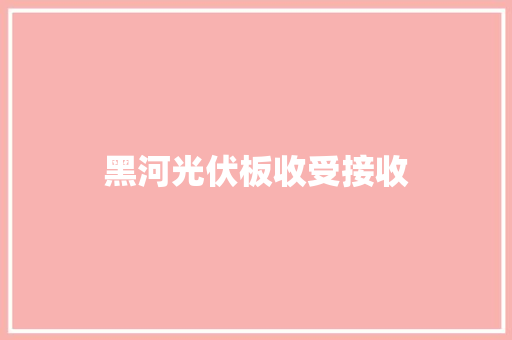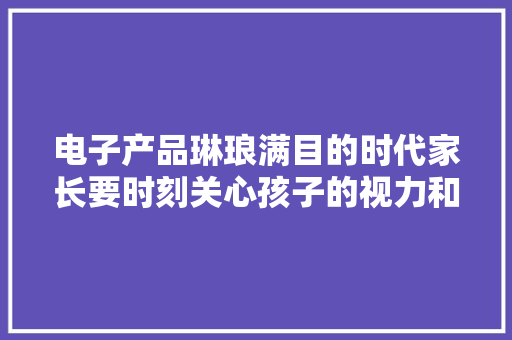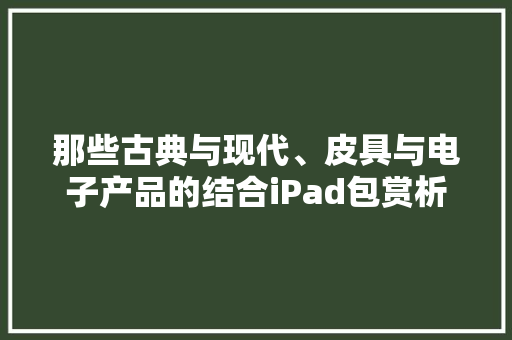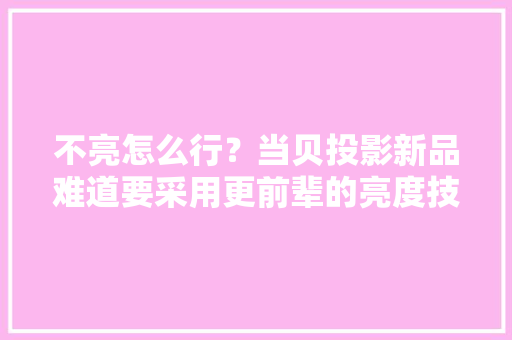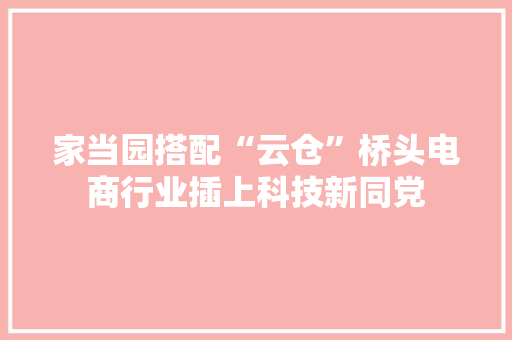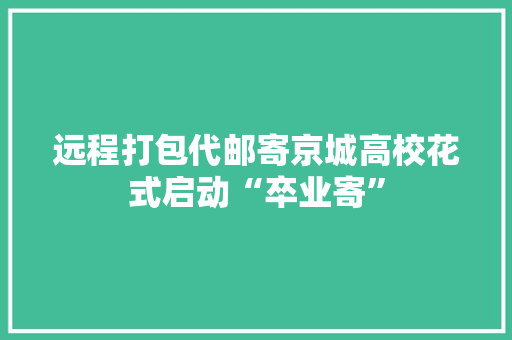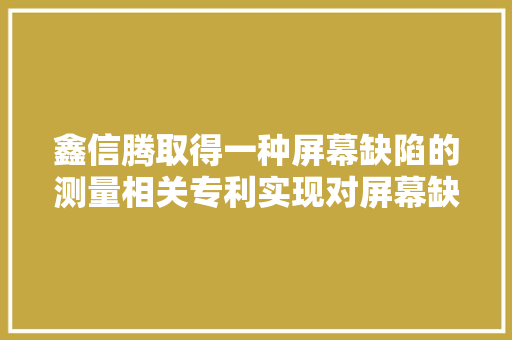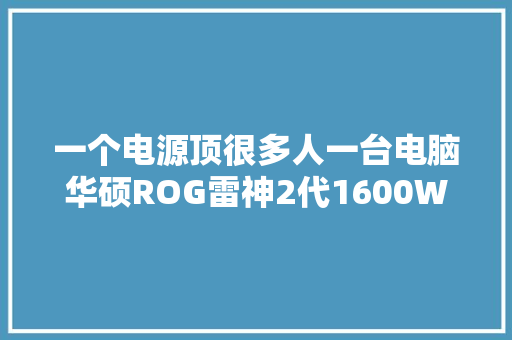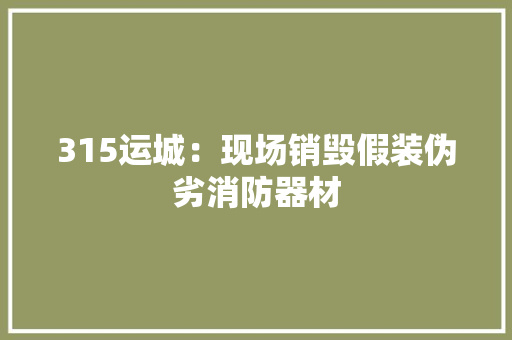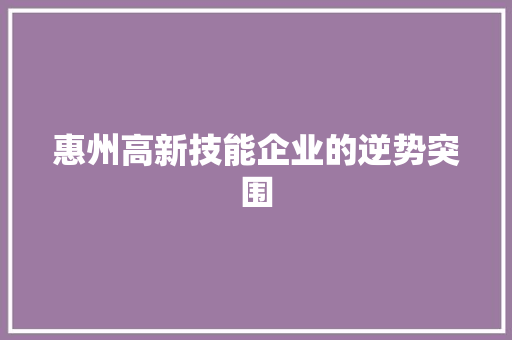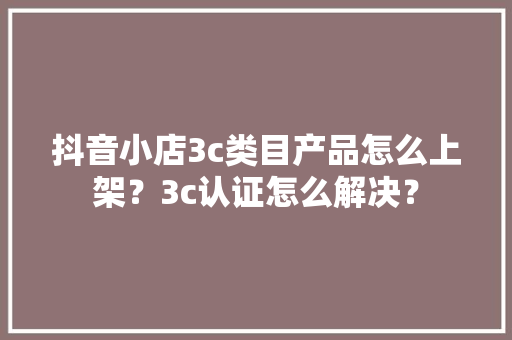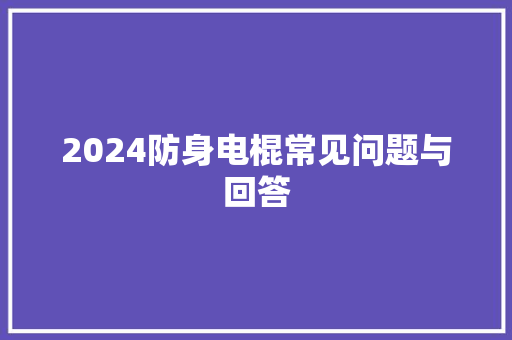女性主体性是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各类力量,自觉哀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办法、知识水平、人格塑造、生理康健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表示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1]。在外婚制和从夫居制的客不雅观条件下,由于屯子女性的寄托性身份与外人角色,其主体性常常与她的父亲、丈夫、儿子紧密联系,屯子女性的人生归属和意义天下屈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逻辑展开[2]。快手类短***平台的兴起,给屯子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屯子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供应了机会,实质是对屯子女性群体的赋权和增能。在快手短***平台中,有“潘姥姥”“屯子会姐”“刘妈妈的日常生活”等拥有上千万粉丝、有较大影响力的屯子女性***博主,也有最为普通的屯子女性,她们没有浩瀚的粉丝、没有较大的"大众年夜众影响力,但随着快手短***深度融入她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沉默大多数”的屯子女性,也从现实的“边缘性”走向一定的网络“中央”,在主体性呈现与实践中表达出自身的声音与力量。 因此,本研究基于甘肃P村落的个案调查,通过对屯子妇女中的“资深”快手玩家进行深度访谈与参与式不雅观察,详细磋商这些最为普通、同质性较强、没有固定职业、且受教诲程度普遍不高的屯子女性,她们是如何看快手、如何玩快手、如何用快手的?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剖析快手的利用对屯子女性活动空间的拓展,屯子女性主体性在网络中的呈现与重构,以及屯子女性主体性在线上线下的互构与再生产。 (一)从抽象到详细的女性主体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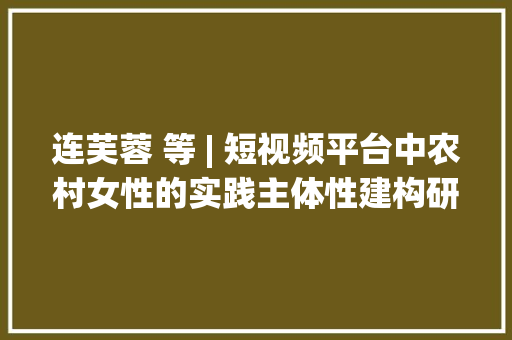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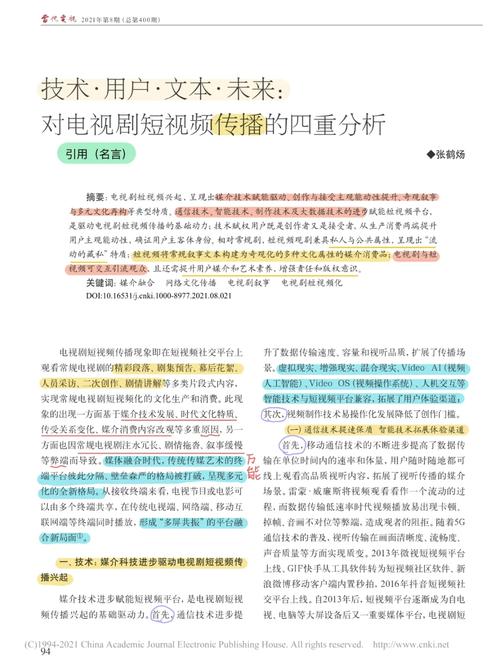
一样平常来说,关于女性主体性的研究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西方女性主义,一个是海内实证的女性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传统女性主义与后当代女性主义两大理论形态。传统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阐明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付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紧张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3]。后当代女性主义质疑女性实质主义,认识到女性是作为男人对立面的“他者”而存在,而所谓的“女性气质”并非是女性生来就具有的,而是在男权社会下由男性制订,并通过一系列逼迫性社会文化塑造,使其固定化、实质化[4]。他们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是理性的、具有认知能力的主体,即女性的自我与道德虽然是不同于男性的,但实质上这种女性的道德仍旧是手段—目的的工具理性,是理性主体的表现[5]。
海内的女性研究一方面继续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主体是一种理性主体的假设,从本土实践出发,关注女性主体行为中包含的大量“策略”,认为女性正是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意义[6]。另一类研究认为女性自我所具有的主体是一种情绪主体,女性以“情绪”为基点实践着自我幸福并进行着意义的阐释,凭“感”觉办事,不计客不雅观后果,在她们认定的事情上不计代价与本钱,强调感想熏染性体验,重视心的感想熏染,不按理性和策略出牌[5]。从后来的研究来看,有不少学者都试图冲破对屯子妇女主体性是策略性还是情绪性的争执,或以屯子妇女在家庭人情中的行为和角色的变革,去认识屯子妇女主体性建构的新变革和社会意义,认为屯子妇女主体性建构的突出标志是冲破传统父权制下以男性为中央建构起来的规则体系和意义确认系统,并自我制订行为的规则和确认行为的意义[7]。或通过对皖东村落落妇女“做会”征象的深描,创造在仪式过程中,村落庄女性主动建构起公共的空间与舞台,并通过集体演出和社会建构实践,建构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隐性权力”和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代价与文化象征体系[8]。这些研究都通过详细深入的事宜或征象“深描”,突出屯子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性子和实践特色。
短***平台的异军突起,为屯子女性带来了参与和表达的新空间。短***平台通过身体叙事、关系叙事和场景叙事为女性在短***中自我展现供应赋能支持。女性在短***中借由基于身体、关系和场景的叙事表达着自我,在一个个“小叙事”中,塑造了更多样的女性形象,其同性的关系也愈加和谐,并得到了男性的支持和理解,乃至还在两性中有主导权[9]。短***平台的技能赋权,带来了屯子女性的“可见性”(visibility)[10]。在短***这一新媒介的影响下,村落庄女性从主流媒体的边缘位置建构中逃脱出来,重塑自身形象得到一定话语权,并利用社交媒体将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从周围的熟人社交扩大为全国范围内的网络社交。但也有学者通过呈现屯子妇女快手平台展演检视赋权效果,创造其赋权存在经济收入的“实”与“虚”、虚拟“中央感”与现实“边缘性”、经济收受接管与社会排斥的张力等后果,呈现出主动的被动性、主体的客体性、瞥见的看不见性等特点[11]。
更多的研究关注村落庄女性在短***中的自我呈现以及背后的权力宰制。中国村落庄女性短***呈现具有“类型多样化、内容多元化和形象立体化”的特点,但看似自由的表达背后却隐蔽着意识形态的束缚与操控,包括传统两性关系、城乡关系和成本逻辑三个方面[12]。从身份叙事的角度去看,一方面,数字平台授予屯子女性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利,屯子女性博主以身体作为“入场”的可支配资源,以自身的视觉逻辑积极开展身体叙事,在交往和抗争中展现与自然互构的粗粝身体;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仍以或隐或显的办法操纵着她们的身体呈现,并通过强调“自我赋权”叙事,将普遍的个体困境与系统性的构造问题相分离。由此,为平台所监视的身体成为自我规训的产物,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沦为可获利的商品,性别文化中的身体难逃主流的性别秩序,城乡二元构造下的身体仍需接管城市群体的想象与裁剪[13]。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短***中屯子女性的形象表达、行为特色等供应了有益的思考。但依然存在一些不敷:一是从关注主体上来看,多是一些在短***平台拥有较多粉丝、较大影响力的屯子女性,或是屯子女性中的分外群体,如留守妇女[14],或是将屯子女性作为一个泛泛的整体,而对付大多数的普通屯子女性则很少予以关注;二是从关注内容上来看,将研究焦点紧张聚拢于短***中的形象呈现与话语实践剖析,缺少将线上与线下勾连的视角。因此,我们将不仅关注普通屯子女性在线上与线下的主体性表达与实践,同时将研究视野由单一的线上或线下拓宽至线上与线下的相互影响,关注屯子女性的主体性在线上与线下呈现的差异性与互构性。
这里须要解释一点。我们的研究工具是屯子中最为普通的家庭妇女,受教诲程度普遍不高,紧张以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照顾及个体经营为主,相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研究结论只能阐明这个群体在打仗快手平台过程中的变革及实在践主体性的特色,无法延伸至其他一些受教诲程度较高或粉丝数量浩瀚的屯子女主播的状况,但大概这便是“社会变革”的底层性与日常性的最好表明。
数据剖析紧张根据主题剖析方法的原则和步骤进行:①熟习数据:整理访谈文本资料,将数据转录为书面形式,反复阅读数据,记录最初的想法;②天生初始编码:按照不同的特色对全体数据进行初始编码,整理与每个编码干系的数据;③探求主题:将编码整理成潜在的主题,网络与每个潜在主题干系的所有数据;④回顾主题:检讨主题与初始编码的同等性,确定不同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⑤定义和命名主题:持续剖析以细化每个主题的细节,以及剖析所讲述的整体故事,为每个主题天生清晰的定义和名称[21],示例见表2。
参考文献
[1] 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不雅观的一种新解读.妇女研究论丛,2004,4:1015+60.
[2] 杨华.隐蔽的天下:湘南水村落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Ⅰ.
[3]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本出版社.1998:11.
[4] 姜晨.试论后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中女性主体性的重新建构.文学界(理论版),2010,4:280282.
[5] 崔应令.村落庄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落的研究.社会,2009,2:7998+224225.
[6] 李霞.寄托者还是建构者?——关于妇女支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1:8287.
[7] 王会,杨华.规则的自我界定:对屯子妇女主体性建构的再认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12120.
[8] 陆益龙.仪式、角色演出与村落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皖东 T 村落妇女“做会”征象的深描.中国公民大学学报,2017,2:97107.
[9] 陈吉.身体、关系与场景叙事:短***的女性参与和赋能策略.当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2:114121.
[10] 古宸璨.快手短***中屯子女性的“自我书写”.视听,2021,9:166168.
[11] 卫小将,黄雨晴.“瞥见的看不见”:网络自媒体赋权屯子妇女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3,5:7384.
[12] 栾轶玫,张杏. 中国村落庄女性短***的自我呈现与话语实践. 传媒不雅观察,2021,7:3947.
[13] 陆新蕾,单培培.可见与不可见:短***平台中屯子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与写作,2022,11:4250.
[14] 石义彬,邱立.弱者的力量:生命进程视域下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与传播评论,2021,5:1327.
[15]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剖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8396.
[16] 高鼓吹.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09.
[17] 周冬霞.论布迪厄理论的三个观点工具——对实践、惯习、场域观点的解析.改革与开放,2010,2:192193.
[18]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40.
[19]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18393+207.
[20] 杨金海.人之存在的主体性三题.中州学刊,1995,5:3842.
[21] V.Braun.V.Clarke.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2006,3(2):77101.
[22] 何志武、董红兵.短***“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落落的野外调查.***与传播评论,2021,3:1423.
[23] 贾海峰.对“重新部落化”的解读.群文天地,2012,13:184.
[24] 俞海山.中国消费主义解析.社会,2003,2:2527.
[25] 费孝通.江村落经济.上海:上海公民出版社,2007:102103.
[26] 张诚,刘祖云.村落庄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7+163.
[27] 董磊明.村落落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5157.
[28] 胡全柱.文化自觉视角下村落庄公共空间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269.
[29]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研究,2010,5:167191+245.
作者单位:
连芙蓉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朱 玮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1-0082-11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2XSH024);兰州大学中心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1lzujbkydx066)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4.01.007
收稿日期:2023-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