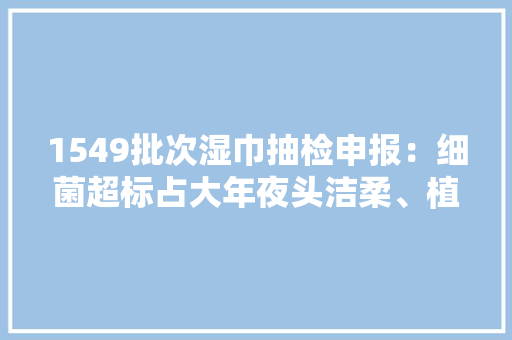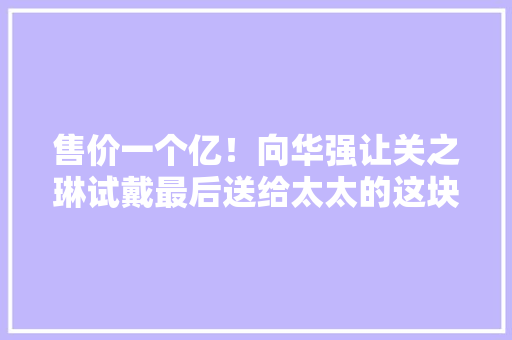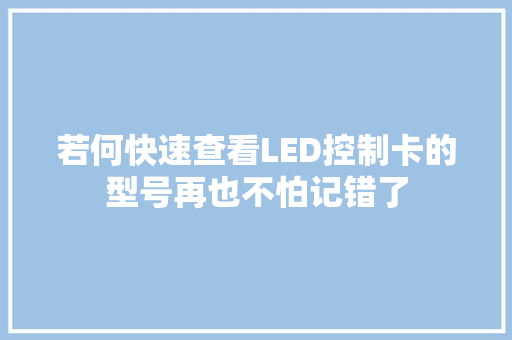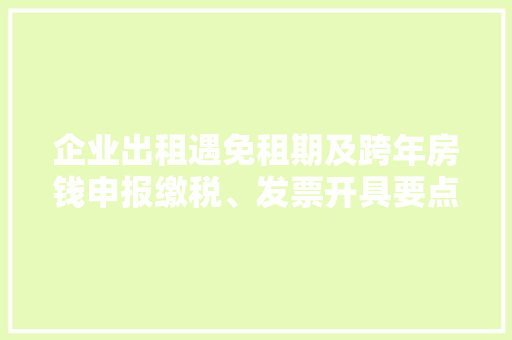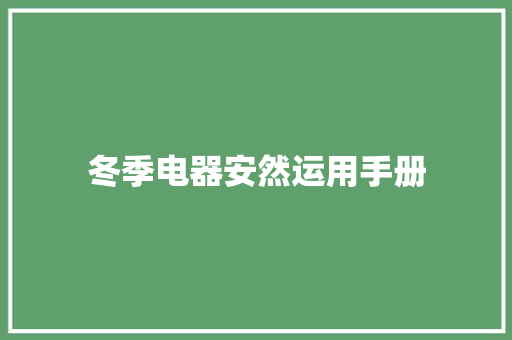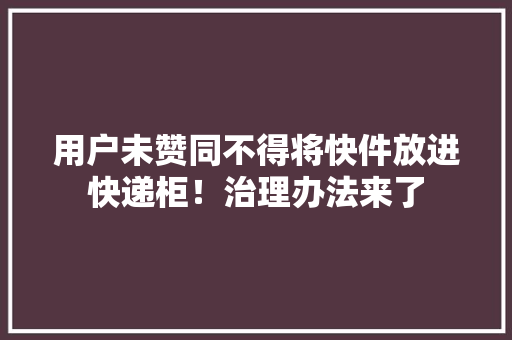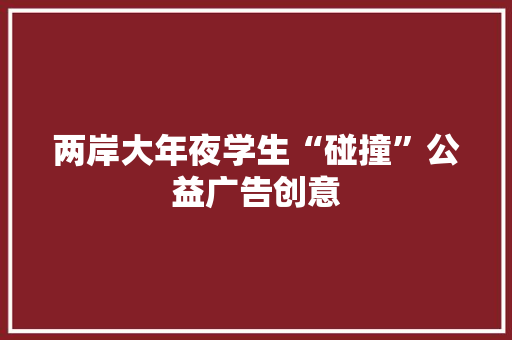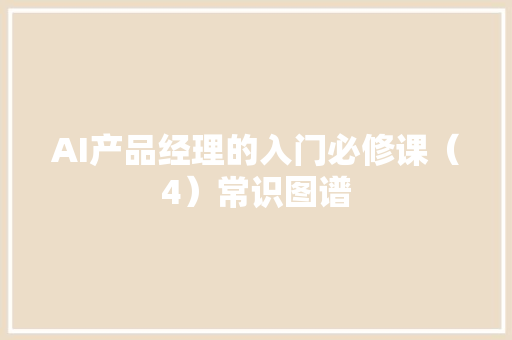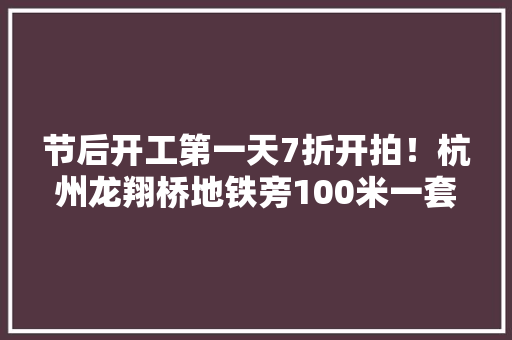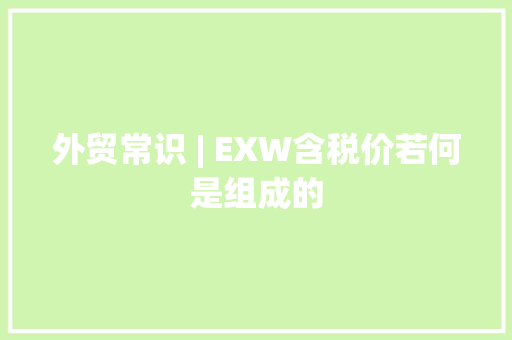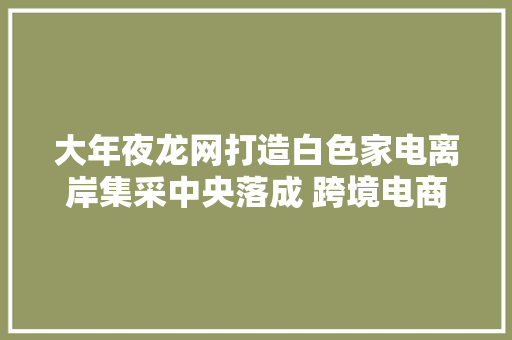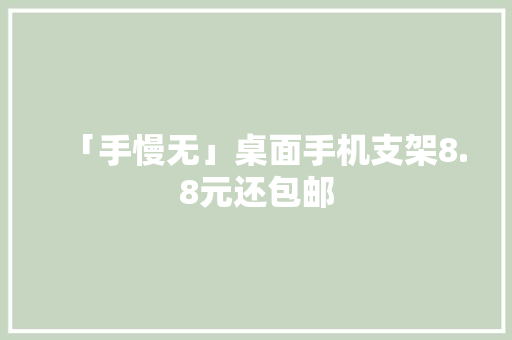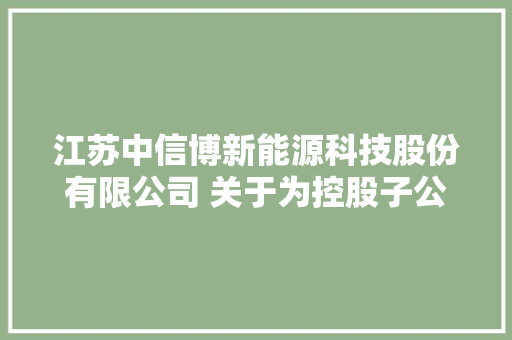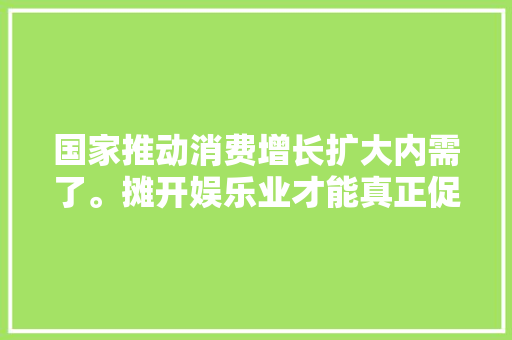图②:曾经厂房上的奋斗口号如今依然清晰可见。
图③:如今在桂林旧货市场依然能淘到二厂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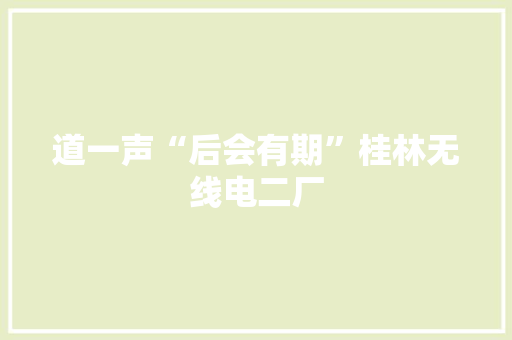
□本报苏展 文/摄

电子工业曾是桂林的支柱家当,产品一度霸占全广西半壁江山。这个中,收录机算是桂林制造的浩瀚电子产品里颇具代表性的一款。曾经漓江厂生产的“漓江牌”和长海厂的“芦笛牌”收录机都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牌子。而桂林还有一个厂当时生产收录机与前二者可以说是并驾齐驱,那便是本日老厂故事的主角——桂林无线电二厂。
“这里不是无线电厂,你还要往前走”
1966年6月,24岁的罗碧波参军队复员。他原来打算回到从军前的学校桂林冶金地质专科学校(桂林理工大学前身)连续念书,但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学校时局混乱,他再三思考,决定去工厂上班。
“这样,下个星期来调你,分配你去轮胎厂吧。”桂林市劳动局里,管事的人这样跟罗碧波说道。但是,一周后,当他再来报到的时候,劳动局改变了决定:“我们桂林工业刚上马,轮胎厂是中南局办的,不是我们桂林办的,现在桂林办的这些厂急需复员兵,你去市重工局报到吧。”
上世纪60年代,像罗碧波这样的中专生同时又有部队磨炼经历,是各大工厂非常欢迎的人才类型之一。“你想去哪个厂?”重工局管事的人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工厂牌号,让罗碧波自己选。罗碧波看了一圈下来,一个之前没怎么听说过的厂映入眼帘——桂林市无线电厂。在部队时,他就常常参加野外电台通信演习,对无线电有一定理解。“那就这个吧。”
而罗碧波并不知道,这个厂在3个月前还只是一间小小的预备处,厂房都没有,最初建厂职员只有30人。
此时,漓江厂还是桂林机器工业学校(桂林电子科大前身)的附属工厂。在市里的安排下,学校把一块平时学生演习用的厂房拨给了刚起步的市无线电厂。“当时我去厂里报到,走到漓江厂大门时,以为这是无线电厂,别人说不是的,还要往前走……”
连续走,罗碧波还是没瞥见什么工厂,又掉头,有个朝阳小学(现在的汇通小学),从小学阁下走过一段烂泥巴小路,才瞥见一片平房……面前的这个工厂显然和罗碧波想象的不太一样,这种差距跟不远处的漓江厂比起来就更明显了。
既来之则安之,这里便是无线电厂,不是漓江厂,间隔摆在面前,罗碧波选择“往前走”,留下来。厂房基本是平房,宿舍也是简陋瓦房,刚到这里的职员基本都是复员军人,大家对吃苦刻苦都有充分准备。
就在这片黄泥地里,桂林无线电奇迹生根抽芽。
年产上百台军用电台,受中心军委通报表扬
虽然一开始桂林无线电厂起步相对有点寒碜,但很快上级就源源不断地将资源向这里调拨过来。像罗碧波这样懂技能的复员军人也越来越多,中心还特殊从北京调人过来,个中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的技能职员,以此支持桂林无线电奇迹发展。
桂林曾经有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和八厂(没有六厂和七厂),但许多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摸不清。
实在,最初桂林就只有这一个位于六合路上与漓江厂毗邻的市无线电厂。后来该厂分出一部分资源建立市半导体厂,在会仙路6号,是后来的桂林市无线电一厂。再后来又分出去一部分,成立市无线电元件厂,厂址在漓江路13号,此乃后来的桂林市无线电三厂。而最初这个厂则为后来的市无线电二厂,由此分成的一厂、二厂和三厂属于一胞三兄弟。而其他的四厂、五厂、八厂则是后来由其余的集体发展而来,有机会另开篇章分享。
大略地说,如果桂林无线电这几个厂是一个家族,那么一厂、二厂、三厂是“亲兄弟”,其他几个是“表兄弟”。而二厂便是这个家族的“老大”(以下均称“二厂”)。
二厂建厂初期从事示波器生产,这也让二厂成为全广西最早能够生产电子整机产品的工厂。1968年,二厂又在广西率先开拓七管二波段全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1969年批量生产。
1969年,国际形势溘然紧张起来,备战号角吹响,全国“三线培植”风起云涌。这一年,隔壁从属国家电子工业部直管的漓江厂彻底改为了军工生产厂,而属于桂林地方国营的二厂也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军工任务。
“接到军工任务后,此前生产的民品就转给其他厂做了,大家集中资源搞军品。”当时厂里分了两批人,一批人去天津764厂学习引进一款军用电台,而罗碧波所在的一批人是去南京714厂学习引进另一款军用电台。
说到南京714厂,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但要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大概大家就立时感到亲切起来,用本日算轻人的话说“DNA动了”。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志愿军英雄王成气吞山河的呼唤,影响了几代人。影片中,王成呼喊时所利用的电台,正是南京714厂自主研制的产品,在抗美援朝沙场上发挥了主要浸染。而罗碧波他们去714厂学的便是王成同款电台。能去学习引进这款“英雄产品”,对付当时的“罗碧波们”来说是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
不过,三个月学成归来后,上级决定让二厂集中资源生产天津764厂的那款军用电台,而南京714厂王成同款电台则与二厂有缘无分,擦身而过。
“天津764厂的这款军用电台也是非常主要的一款军用通信产品。”生产任务下达后,全厂投入到这款军用电台生产中。罗碧波时任考验科科长,这个科有十几个考验员,他们的任务便是对这个产品各个部件进行考验把关。
“你比如生产出一个滚轮部件,那么我们任务便是对这个滚轮进行测试,让它连续滚动一万次,看看它的镀银层会不会脱落。摇完一万次一样平常要一天一夜。”
“又比如冷热冲击试验,我们将一个产品部件置零下四十度的环境后拿出来,立时放进五六十度的环境里,看它开不开裂。开裂就不合格。”
一个产品从零件到成品入库,须要签三个字。第一个便是考验科罗碧波的具名,第二个是厂长的具名,第三个是驻厂军代表的具名。少一个具名就要返工。而常常是在罗碧波这里就被返工了。产品返工,进不了库,任务完不成,大家拿不到奖金。有人送他外号“扛个竹竿走路,不会转弯”。
“电台,那是指挥千军万马的,说弗成就弗成。”这一句“弗成”一说便是十年,直到1980年“军转民”,二厂停滞军工生产。
桂林市志这样记载这段历史:“1970年,桂林市无线电二厂从天津764厂引进技能生产军用电台,连续几年生产,年产量在100~200台之间。该机性能良好,质量可靠,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确保通信畅通,受到中心军委果通报表扬。”
“我们的收录机,想买要靠抢”
桂林的电子工业曾是支柱家当,在“军转民”的浪潮下,几家电子工厂都开启了自己的民品求生之路。个中漓江厂、长海厂与二厂等代表厂都不谋而合地在这一期间选择了收录机这一产品。
漓江厂的产品叫“漓江牌”,长海厂的叫“芦笛牌”,二厂生产的产品先后利用了“桂林牌”“山水牌”“丹桂牌”“爱丽华”等名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都走上了“引进、消化、接管”的道路,分别从喷鼻香港吸收散件组装收录机。
不同的是,漓江厂和长海厂两个厂皆属国家电子工业部直管,而二厂属于地方国营,以是漓江厂和长海厂的产品生产出来基本是拉到全国各地发卖,同时他俩还生产电视机;而二厂紧张做收录机,更多是做事于本地至广西范围内。以是,“漓江牌”和“芦笛牌”在广西外的有名度更高,而二厂的收录机则在本土市场拥有高霸占率。换句话说,本日如果一些老桂林家里还留有收录机这个老物件,大概二厂的产品会更多一些。
从喷鼻香港引进的技能加上桂林本身的电子工业根本,让桂林生产的收录机质量出众,形状也时髦,一时成了市场上的“喷鼻香饽饽”。
“喷鼻香”到什么程度呢?想买要靠抢。
当时实施操持经济,二厂的产品出厂后原则上拉到桂林市五交站,由市五交站收购后,再分发到各个县区五交站发卖。但收录机最火爆的时候,桂林市五交站是收不到多少二厂的收录机的,由于从贵州、四川、云南等地五交站来的人会自己开着大卡车到桂林,等在二厂门口抢货。
“有时,他们抢不到货,还会吵架、斗殴。”彼时,罗碧波仍在卖力考验事情。收录机卖得最火爆的时候,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罗,这个东西只要一响就出货吧。”
“那可弗成,合格证可不能随便贴,肯定要严格哀求。”
为国家创汇做出贡献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海内收录机市场日益萎缩,产品过剩。漓江厂、长海厂的收录机生产先后停滞。
而二厂依然坚持着大批量的收录机生产,乃至越来越忙。由于他们在这一期间走上了合伙出口的道路,由海内市场转战外洋。
《桂林市志》记载,1988年,二厂与港商合伙兴办了桂林爱丽华电子有限公司,以生产收录机为主。进入90年代,该厂狠抓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形成规模经济。
1990年,与喷鼻香港爱高电子有限公司互助生产各种国际盛行格局的收录机和音响等10多个规格品种,产品95%以上出口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1995年出口收录机达60万台。
当时,爱高是环球有名电子产品生产商,产品是销往全天下的。爱高将部分外洋订单转给二厂旗下的爱丽华电子有限公司加工。海内虽然收录机已经饱和,但是外洋空间还很大,特殊是非洲地区。以是在90年代中期,各个国营大厂开始大规模遭遇市场冲击,改制,职员下岗时,二厂居然还在招人。
有资料统计,1995年,二厂共有职工1122人,个中工程技能职员70人,辖有桂林爱丽华电子有限公司、桂林星际电子有限公司、桂林航空电子器材公司、永兴电器厂等多家独立核算单位。占地面积460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10793平方米;各种生产线9条,电子专用设备600台。
要知道90年代正是国家缺外汇的期间,此时二厂的爱丽华能为国家创汇,用桂林话说是很“牛鬼”的。有数据显示,1995年,二厂生产收录机68.98万部,个中出口68.78万部,创汇1000万美元。
“1996年和1997年是最忙的时候,订单火爆,有时候,一天就要做五六千台收录机出来。”罗碧波记得,当时由于订单太多,厂里把一个仓库都改成了生产线,每天四条生产线,加班加点,四五台大卡车等着拉货,职员不足,厂里还去各个屯子招临时工。
而这一期间,同为曾经收录机生产大户的长海厂和漓江厂则都在各自经历自己的“至暗时候”。出口这条路让二厂的收录机比同期起步的“漓江牌”和“芦笛牌”收录机多卖了近10年。但这样的红火到2000年前后,也随着收录机外洋市场逐渐饱和开始极速降温。而另一方面,虽然二厂此前一贯有大批量订单,但几年下来竟没有赚到钱。
“我们的加工本钱太高了。”一贯与质量打交道的罗碧波对此影象深刻,二厂为港商爱高做加工,质量标准由爱高制订和把关,在抽检过程中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机子不合格,那么整批订单可能就要报废重做。产品报废率很高的情形下,二厂却依然坚持生产,工厂灯火彻夜通明的背后实在是返工太多造成的机壳废物堆积。
既然这样,为何还要接单呢?由于当时能创汇的企业太难得了,即便是亏本也在坚持做。这么一来二去,二厂忙劳碌碌几年下来,自己非但不赢利,反而欠了一身债,逐步地,爱高也停滞了与二厂的互助。没有订单,自身又欠下巨额债务,导致企业周转困难,寸步难行。2011年,二厂完成改制,曾经辉煌至此告一段落。
时至今日,二厂尚在,但早已停滞生产,昔日风光随着那些桂林人家中角落里常年未再通电的收录机一同老去。这片年近花甲的旧厂区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默默静候新的希望到来。
静候佳音,暂道一声“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