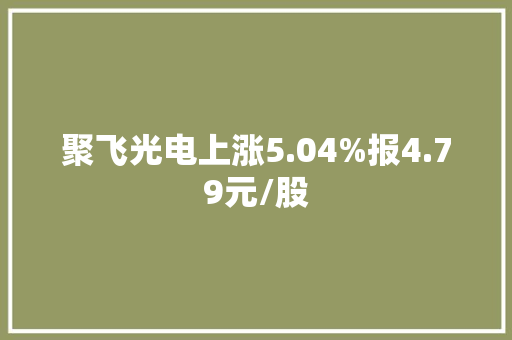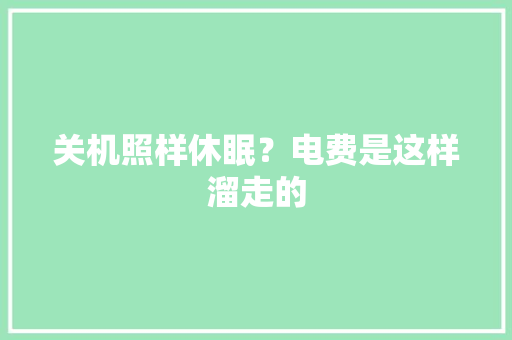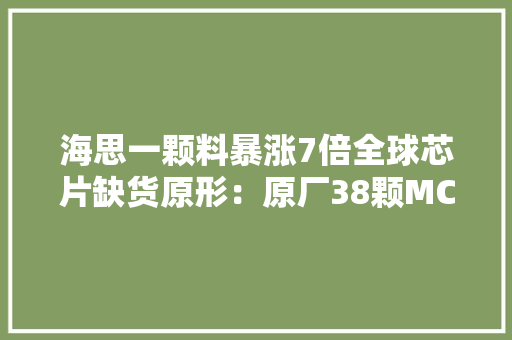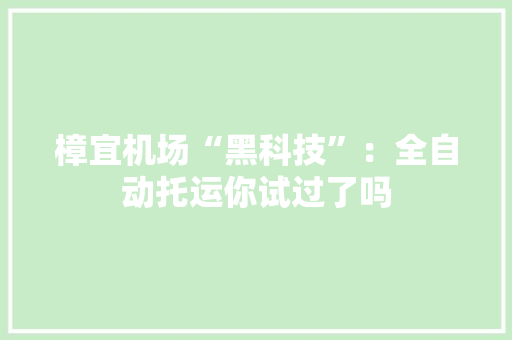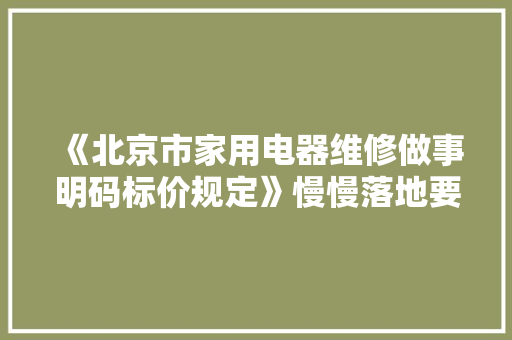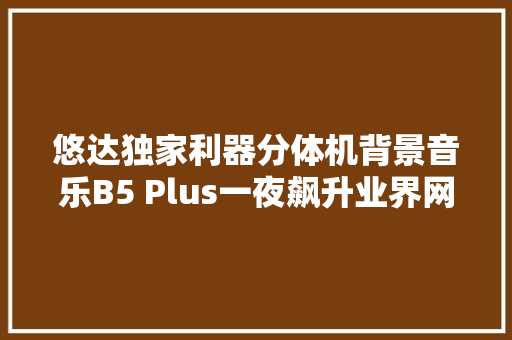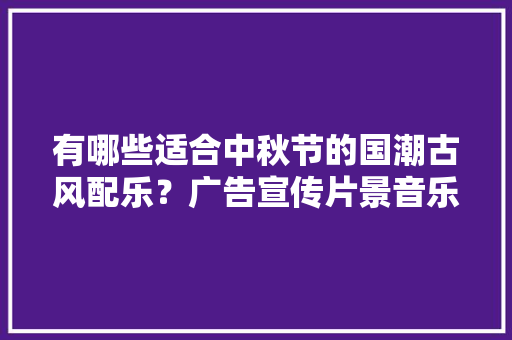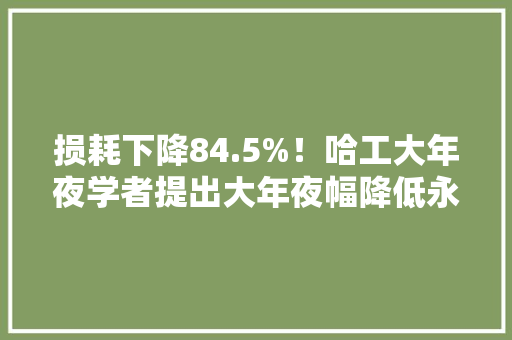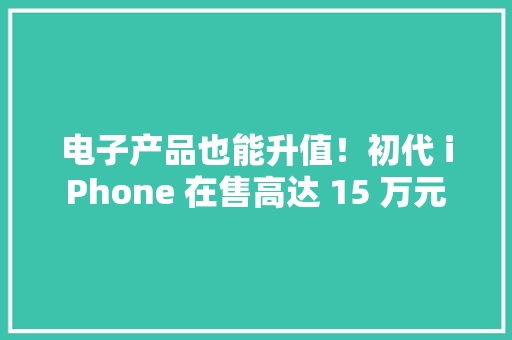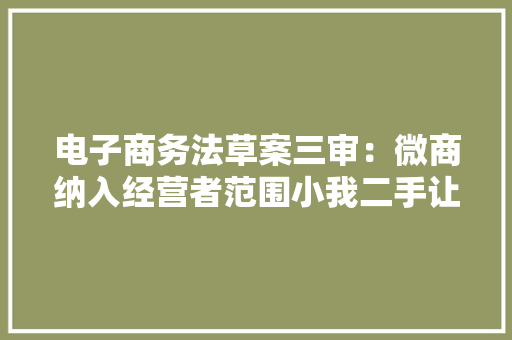魏征西将军邓艾,因与钟会、卫瓘不睦,终极含冤惨去世。人所共知。
讽刺之处,是逆贼钟会“家门得全”,除置留洛阳的养子(钟毅)被戮,其兄钟毓一系未受牵连。冤杀邓艾的卫瓘、则凭弹压钟会的“大功”位极人臣,荣宠三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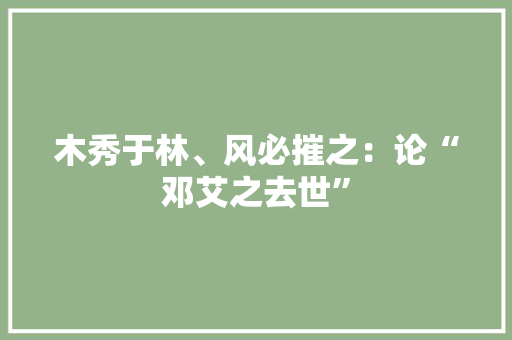
西晋开国,为曹魏勋贵平反;诸葛诞、王凌等淮南三叛的“首逆”子孙都得赦免,邓艾有功无过之人,却被彻底遗忘。

邓艾家属流徙西域,孙邓朗在泰始九年(273)才经“法外开恩”、得到“郎中”(警卫员)小官,且艾依然身背“叛逆”恶名。
因此其受戮始末,便尤其值得磋商。
邓艾之去世,缘故原由大致有三:
其一是误解司马昭心意;其二是骄矜自大;其三是出身寒门。
本文共 4100 字,阅读需 8 分钟
司马昭的“心意”司马昭伐蜀,本无进取之心。其本意是通过伐蜀“洗清罪名”,之后加官进爵、图谋嬗代。
灭蜀之战前三年(260),司马昭欲进爵“晋公”,之后废帝自主。魏帝曹髦闻讯,不愿“坐受废辱”,奋起反击,遭太子舍人成济弑杀。
帝曰:“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汉晋春秋》
成济后台是中护军贾充。充,司马昭亲家,其长女嫁昭子司马攸。
白日弑君,滔天算夜罪。连一向敦睦司马氏的陈泰(陈群子)都忍不住大骂“杀贾充以谢天下”。
可见当时矛头所指。
(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即陈泰),卿何以处我?”
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
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晋纪》
注:“有进于此”即归咎司马昭。
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
因此,曹髦的继任傀儡天子曹奂,登基伊始(260),累次给司马昭进爵“晋公”,昭皆辞而不受。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增封二郡,并前满十,加九锡之礼。
文王固让乃止。--《魏书三 陈留王本纪》
“让爵不受”非司马昭有谦恭之心。
一个白日弑君的贼子,有何廉耻?实在是彼时“天下汹汹”,司马氏声名散乱,不敢接管罢了。
纯因发怒曰:“贾充!
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
纯曰:“崇高乡公何在?”众坐因罢。--《晋书 庾纯传》
以是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战,并非司马昭有进取之心,而是“略建功勋,平息众怒”的小伎俩。
须知,彼时满朝文武,仅有钟会一人支持司马昭伐蜀。且不说钟会后来还反了。
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魏书二十八 钟会传》
在此背景下,作为三路主帅之一的邓艾,也就该当尤其理解“主君心意”。艾最初对伐蜀不置可否,惹得司马昭不悦,嫌其“政治觉悟太低”。
注:三路主帅,即钟会、邓艾、诸葛绪。
大军八月出发,十月刚刚抵达剑阁,司马昭便谎称“捷报频传”,接管了晋公之位。又授意魏帝给自己加九锡,一如魏武故事。
注:《魏书三 三少帝纪》未详载司马昭受晋公韶光,查《晋书 文帝纪》可知在当年十月。文多不载。
可见伐蜀便是“障眼法”。彼时的司马昭,目的既达(进爵晋公),便已做好班师准备。
而邓艾兵行险招,偏师深入,击溃诸葛瞻、逼降刘禅之后,在成都大封文武。又给司马昭上疏,哀求“暂缓械送刘禅赴洛阳”,而要“就地安抚”以“给吴国君臣做榜样”。
今宜厚刘禅甚至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
司马昭本便是借着伐蜀的“由头”,替自己洗清罪名,重修威望,好图谋嬗代大业。邓艾可倒好,得陇望蜀,得蜀望吴,还“心系天下”起来!
“不上道儿”的程度,乃至于是。
彼时的环境,一言蔽之:
嬗代是里子、伐蜀是幌子、钟会是贼子、邓艾是锤子。
荒诞至此。
骄矜自大的征西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客不雅观评价,邓艾在成都的一系列“越轨行为”,虽有善心,却也并非全出于“家国激情亲切”和“统一壮志”。
艾在成都,擅自署置,表封刘禅为“扶风王”。
(艾)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旁边。--《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
这是一个很悖逆的行为。
由于彼时的司马昭,刚刚进爵晋公,不过公爵而已。若封刘禅为王,岂不是平白压了司马昭一头!
邓艾还提出,可以将刘禅安置在扶风郿县的“万岁邬”中,即昔日董卓所筑之郿坞。更是令司马昭愤怒。
艾在成都,擅署官爵
邓艾不仅要给刘禅封王,乃至最开始还要给诸葛瞻封王。
绵竹之战时,艾作书于瞻,称若归降,必表为琅琊王。
注:诸葛家族出自琅琊阳都,故以此相诱。
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蜀书五 诸葛亮传》
琅琊阳都葛氏,在彼时是个“颇为敏感”的家族。
因诸葛诞的“淮南(第)三叛”结束未久,彼时竟逼得司马昭亲征。而伐蜀“三路主帅”之一的诸葛绪,又因“会师失落期”而被钟会褫夺兵权。
会与绪军向剑阁,(钟)会欲专军势,密白(诸葛)绪畏懦不进,槛车徵还。--《魏书二十八 钟会传》
诸葛诞、诸葛绪皆琅琊葛氏,与亮、瞻同族。而仕宦魏国的诸葛氏、在伐蜀前夕的“连续变故”,一定令司马昭心生猜忌。
邓艾表奏诸葛瞻为“琅琊王”的行为,或是阵前诈术,但听在司马昭耳朵里,想必是另一种声音。
情由同上,彼时的司马昭爵止“晋公”,邓艾连续给蜀国君臣表奏“王爵”,又是何意?
再加上邓艾亲信在成都敛财索贿,“大奸宦”黄皓因此幸免于难。
亦可见艾彼时骄矜自大,恐怕已非纯粹的“心系天下”。
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及邓艾至蜀,闻皓奸险,收闭,将杀之。
而皓厚赂艾旁边,得免。--《蜀书九 董允传-附传》
邓艾谢绝将成都府库的金银财物转运洛阳,又质押刘禅不遣,美其名曰“安抚吴国”。
无论其本心如何,在司马昭眼中,这毫无疑问是“反迹已露”。
扞格难入的“丛草吏”人很难分开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出身、有时又会成为一种羁绊。
邓艾出身低微。其本职阐明众说纷纭,翻译成当代汉语,大致便是屯田地区、库管下面儿的“帮工”。
(艾)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
注:“稻田守”是农官名。“丛草吏”指代为何未详;大约是低级杂吏。
艾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
三国两晋南北朝,可谓“皇权政治崩塌、门阀政治崛起”的时期。
彼时以“门第阀阅”论高低,贵游子弟出将入相,美其名曰“清选”;寒门贫士不得发迹,被讥笑为“浊途”。
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孟)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魏略》
更不用说各郡县还有“中正”来考察门第品级,但凭出身,不论才干。
司马懿当政时,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把腐烂僵化的政策,在制度上加以巩固。
以“血统身份”论资排辈的万恶制度,自然是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糟粕。
但邓艾偏偏生在当时,因此其卑贱出身,也就显得格外刺眼。
邓艾伐蜀时,年逾七旬。自古未闻如此老朽,依然能“心存反志”。
艾功名以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
我学识浅薄,所知最年长的“造反上位”者,便是五代时的后唐明宗李嗣源,其篡位时年逾六旬。
注:明宗叛乱事出不得已,不多展开。
邓艾冤去世,不得平反。实在无关其叛乱与否。只关乎其“门第出身”。
门阀叛乱者,西晋皇室皆宽恕赦免。
上文提过的钟会、诸葛诞便不说了;“淮南首叛”的王凌,自主新君(楚王曹彪),滔天算夜罪,子嗣却得到赦免。
情由极为荒诞,是“齐王曹芳终极被司马师废黜,以是王凌谋废齐王,经实践的证明是精确的”。
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齐)王竟不敷以守位。”--《晋书 武帝纪》
注:司马炎的脑回路颇为怪异,彷佛比司马衷强不了多少。
王凌出身太原王氏,是诛董卓的王允之侄。“太原王”何等地位,不必赘言。
注:崔卢李郑王,是北国五大高门,个中王即“太原王氏”。
“淮南次叛”的毌丘俭和文钦,钦子文鸯、文虎亦得赦免。鸯后来还立功他乡,成了西晋名将。
文氏祖孙是谯沛人,魏武同乡。自文稷在建安中为曹操骑将而发迹,三代显赫。文鸯、文虎被赦免,亦由高门之故。
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王沈《魏书》
“淮南三叛”的诸葛诞,以公族外戚之尊,其子(诸葛靓)得到司马炎的亲自拜会,显贵无比。
注:诸葛诞之女、嫁琅琊王司马伷。
夏侯霸是夏侯渊子,背反朝廷,亡入川蜀。其嫡系子孙不过流放,未遭杀害。
而渊系诸子,则毫无牵连。霸弟夏侯惠,为散骑常侍、乐安太守;霸弟夏侯和,魏时为河南尹(郡治洛阳),入晋后还成了光禄勋。
注:散骑常侍同“侍中”,天子近臣,秩比二千石;光禄勋为九卿,秩中二千石。
霸亡入蜀,而诸弟显贵如旧
就连曹爽、夏侯玄这些被“夷三族”的司马氏头号政敌,也被从远亲中过继了子孙,供奉爽父曹真,玄父夏侯尚。
嘉平中,绍元勋世,封真族孙(曹)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后。--《魏书九 曹爽传》
正元中,绍元勋世,封尚从孙(夏侯)本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后。--《魏书九 夏侯玄传》
邓艾有功无过、勋书竹帛,末了却落了个“诸子被戮,孙子流放西域”的悲惨了局。
忠与艾俱去世,馀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
其孙邓朗被赐“郎中”小官,也并非“为其平反”,而是“邓艾依然有大罪,只不过念在其束手就擒的恭顺举动,略加恩赐”。
(诏曰)邓艾虽矜功失落节,然束手受罪。本年夜赦其家,还使立后。--《晋书 武帝纪》
投胎确实是个技能活,邓艾命途舛悖至此,徒令后人一声嗟叹。
结语邓艾偷渡阴平,本便是个错进错出的误会。由于“战役发起者”司马昭从未“真正想过”伐蜀。
大军八月出征,十月便急匆匆自领晋公,可见其醉翁之意不在酒。
所为何事,***所知也。
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曰:“司马昭之心,***所知也。”--《汉晋春秋》
邓艾身为诸路主帅中唯一一位兼备“智勇”与“进取心”的军主,一举破蜀,功垂千载。
然而艾入成都、留后主不遣,又不肯送交金银财物;再加先后为诸葛瞻、刘禅“求封王爵”,使得刚刚自领“公爵”的司马昭甚为不悦。
失落去主君信赖的邓艾,被钟会构陷,遭卫瓘追斩,也便天经地义了。
至于邓艾含冤而去世,子嗣废毙流徙。究其缘故原由,是其生不逢时。出身卑贱却屡建殊勋,在魏晋“门阀政治”的笼罩下,无疑会遭到权贵忌恨,导致不以道终。
陈寿所言“邓艾疏于防患,败亡立至”,提要挈领玄机。
邓艾闇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此盖古人所谓“目论”者也。--《魏书二十八 邓艾传》赞语
看得见山峦之远,而看不见睫毛之近。可谓精洽。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阐发展开背后隐蔽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